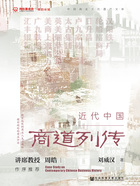
二 汉阳铁厂选址问题
(一)应该如何选址?[7][8]
在交通运输系统尚不发达的时候,铁厂只得尽可能靠近矿源(主要是煤矿和铁矿),以减少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西方近代钢铁企业也皆是以此作为铁厂的选址依据,特别是19世纪50年代英国冶金学家贝塞麦发明了转炉之后,使低成本大规模的生铁及粗钢生产变为可能。这意味着铁厂离矿源越近,就越能够节省成本,那么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将越多。可是,随着铁路、航运等交通系统的日益发展,矿石等原材料的运输费用大幅下降,企业家们对铁厂选址的考量从偏重于矿源逐渐转为偏重于市场。也就是说,厂方更愿意将铁厂建立在对钢铁产品需求量相对较大的、不一定靠近矿源的地区。如此选择的目的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其产品的销售情况,并得到市场的反馈,便于对制铁工艺等进行及时的改进。整体来看,为钢铁厂选址时,应该在综合原材料供给、销售市场、经济和政治环境各项因素之后,找出能够最大限度平衡各方的最优解,以实现钢铁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社会利益(包括经济和政治方面)最大化的双重目标。
(二)选址一波三折
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的时候,打算在广州开办钢铁厂,地点确定在了珠江南岸的凤凰岗。另外,张之洞在调任两广总督之前为山西巡抚,在该任期内便已经对山西境内各个大小矿源一一进行勘探调查,发现该地区煤矿极为丰富,因此早期有在山西建立西式铁厂(所谓西式铁厂,是指现代蒸汽机问世之后,使用机械进行大规模生铁和粗钢冶炼的工厂)的想法。调任广东之后,他便继续带人对粤北地区进行勘探,发现此处铁矿产比较丰富,加之整个广东地区洋务运动正盛,西方国家商行也大多在广州、香港设有代表处,这些条件更有利于采购铁厂所需要的生产设备。因此,起初张之洞盘算,建立铁厂最佳的地点应该是山西,其次就是广东,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在湖北设立铁厂。当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之后,这些炼铁设备并没有即刻随他一起前往武汉,而是继续留在广州凤凰岗等待铁厂的建立。
然而继任的两广总督李瀚章对洋务事务不感兴趣,加之才刚上任,于公于私都极不愿意插手建立西式铁厂的差事。虽然张之洞多次与李瀚章沟通广州铁厂事项,但李瀚章均以不熟悉洋务事务以及清廷筹划卢汉铁路急需钢铁为由推辞,并劝说张之洞就地在湖北设立铁厂。于是张之洞便顺势奏请清廷批准将原本应该用于建广州铁厂的设备全数迁移至湖北[9]。至此,铁厂定址湖北可以说是板上钉钉了,只不过具体地址到底应该选在湖北哪里还未定。
湖北省的铁矿资源丰富,特别是大冶县的铁矿石不仅储量大,而且品质极佳,含铁率高达64%,为“中西最上之矿”。其连续多年产量丰富,甚至受到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23年12月国民政府农商部发行的《中国铁矿志》记载“大冶铁矿在1910年估计储矿量为1.39亿吨,其中水平以上约为1.04亿吨,水平以下约为0.35亿吨”,并且大冶铁矿的开采可以追溯至三国时期,是当时尽人皆知的矿源地。历史记录指出,在1890年,张之洞先后组织15批30人次的勘探队,分别在湖北、湖南、江西、陕西和四川等地进行实地勘探工作,目的是寻找湖北及其周边省份的矿藏(包括铁矿和煤矿),相信张之洞在勘探工作完成之后,也一定会了解大冶铁矿的规模的确是当时矿源之最[10]。
大冶铁矿同时也以产煤闻名天下,这一点从张之洞在1889年9月29日给驻英公使刘瑞芬的信件中可窥知一二。时任北洋大臣,同时也是“洋务先锋”的李鸿章从西方建立铁厂的经验出发,认为远距离运煤使得费用剧增,并且西方国家一直都是“移铁就煤,而非移煤就铁”,极力主张将铁厂建立在大冶黄石港。同时,被后人称作“中国商父”的盛宣怀,实地对大冶铁矿及其周边进行了勘测,发现铁矿源临近江边,又与锰矿源靠近,而锰元素是在炼铁中必不可少的,所以盛宣怀根据自己之前丰富的办矿经验,也赞同在大冶黄石港建厂[11]。
既然建铁厂就是搞企业,当然应该借本求利。作为企业,盈利是核心,而实现盈利最直接的途径无外乎两个——提高价格和降低成本。对于尚未进行任何生产活动的企业来说,其产品能否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以及是否有能力与行业中的老牌企业竞争还犹未可知,因此不会选择通过定高产品价格来实现盈利。所以对于新成立的企业来说,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才是明智的选择。张之洞坚持将铁厂建在汉阳可以理解,但是他为什么要选择在煤铁皆缺的汉阳大别山山麓建立铁厂呢?
(三)兼顾政经,定址汉阳(今武汉汉阳区)[12][13]
实际上,在张之洞心中,如果要将铁厂设立在湖北,大冶黄石港亦是他的最优选择。在他与李鸿章往来的一封书信中说“现拟运煤就铁,炼铁厂自以附近产铁地方为最善”,这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建立钢铁厂的通行做法。只是,张之洞与洋矿师郭士敦实地查勘黄石港时,发现这里地势相对较低,若在此建厂,难免有遭遇水患的危险。然而当时张之洞并不愿放弃在黄石港建厂的想法,多次派洋矿师以及自己的心腹徐建寅带领测绘员前往勘探,直到勘探队最后呈报“该港沿岸平处,皆属被水之区,其高阜仅宽数十丈,断不能设此大厂”,张之洞才将在黄石港建厂的想法作罢。可见张之洞对铁厂地址的判断是正确的,是符合商业规律的。即使黄石港的地理环境不适宜修建铁厂,大可在大冶县境内另觅厂址,那么张之洞为什么固执地选择了汉阳呢?
笔者认为张之洞这样的决定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经济和政治。如果在黄石港建铁厂的话,那么可以说炼铁所需的一切原材料都准备就绪,几乎不会产生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无疑是最理想的方案。大冶铁矿附近虽然还有煤矿和锰矿,可是大冶县地处湖北南部,以丘陵、山地为主,相对平坦的地域只占全境面积的9%。大冶铁矿矿源地处山区,若不能在黄石港建厂炼铁,那就需要开山挖隧道将矿石运出,这无疑又增加了一项巨大的沉没成本(Sunk Cost)。另外,煤矿易碎、易受潮的性质决定其所要求的运输条件要高于铁矿石,因此在气候潮湿且崎岖的山路上运输煤矿,不但增加了成本,更增加了风险,但是对于铁矿石等这类需要提炼加工的矿石的运输,就无须考虑这些问题。从地图上看,山西与湖北之间隔着河南,从产煤大省山西运煤到武汉的距离虽然大于大冶至武汉,但是道路平坦、气候干燥,可以说几乎是零风险运输。因此,从经济角度考虑,当黄石港建厂计划不宜成行时,最好的备选方案应该是在“煤铁两就”的武汉建厂,而非单方面的“移煤就铁”,在大冶境内其他地区建厂。
另外,将铁厂定址武汉比定址大冶更能够留住人才。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的第一家西式铁厂。不同于传统的打铁作坊的制铁方法和流程,工程师们需要了解矿石的鉴定方法与提纯步骤,以便对炼制的生铁和粗钢进行进一步的优化。目的是保证其延展性和韧性能够适用于工业生产当中,特别是铁路、轮船等方面。而炼铁工人们需要熟练掌握工业机械的使用、保养和修理方法。在当时,洋务运动虽然已经开展近30年了,但是其涵盖范围并不大,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等由于鸦片战争而被开放的几个口岸,以及一些交通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这些地区中的民众对于洋务运动的目的和内容有一定的认知,其中更不乏留洋归国的新式知识分子。因此,在这些地方建立西式工厂所遇到的阻力必然小于其他尚未开放的、仍属于小农经济以及封建保守的地区。相对而言,大冶县地处鄂南山区,士绅百姓思想保守,对于建立西式铁厂相当抵制。据记载,洋矿师白乃富在大冶进行勘探时,差点被当地民众砸伤,张之洞听闻此事之后,便说道,若厂址定于大冶,“洋匠亦不能深入”。但是,第一座现代铁厂若无洋技师的参与,是不可能顺利建成的。因此,张之洞既然要引进人才并发挥其专长,以利于快速建成铁厂,就一定要聘请大批洋技师以及留洋归来的新式知识分子。那么为了向这类专业人群提供相对便利和优质的工作生活条件,便于最大限度地留住人才,在省城武汉建厂确实是最优的选择。
再从销售渠道的角度来看,在武汉建厂可达到“地利人和”的效果。武汉是湖北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人口众多,自古便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富裕,整个地区经济也呈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象。特别是开埠通商之后,“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直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可见当时武汉商业之繁华以及临江之便利。张之洞在湖北境内选址建厂的时候,也必须同时考虑生铁粗钢的销售渠道。武汉作为该地区的商业核心地带,其影响力与销售网覆盖的范围都远远超过了大冶。事实也证明,在上海市场开拓之前,中国的钢铁以及煤矿的销售绝大部分依赖于汉口口岸。孙子曾说:“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即所谓地利,就是要在作战时考虑到距离的远近、地势的险阻平坦、地域的宽窄以及死地和生地的利用。总而言之,想要在战场上获胜,明智地利用地理环境是相当重要的。因此,综合考虑了建立铁厂的原材料及销售的地理因素之后,武汉可以总体评价为最理想的经济选择。
在政治考量方面,张之洞在汉阳建厂与他的政治对手李鸿章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几乎可以说是李鸿章间接建立了汉阳铁厂。大家都知道李鸿章是晚清的名臣、重臣,是洋务运动坚定的支持者,中国许多近代企业都是由他创办的,比如著名的轮船招商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另外,李鸿章靠打仗发迹,军事嗅觉敏锐,通过日本吞并琉球、法国占领越南看清了清王朝海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开始筹建北洋水师,至1890年前后将其发展成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规模。当时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不仅手握兵权,而且掌控着多家洋务企业,他的势力不断壮大,这让慈禧颇为担忧。更重要的是,借着工业革命的东风,西方国家的军事发展异常迅速,各种新式武器层出不穷。统兵打仗多年的李鸿章明白,只有武器跟得上时代的发展,才有可能在战争中取胜,落后的军事装备只有战败一种结局。北洋水师建立之时便耗资巨大,此后每年的军饷、武器与军舰的添置和维护费,大部分出自北洋派所创办的洋务企业,剩余部分由国库拨款[14][15]。然而慈禧以“张天朝之威”为由,不顾当时积贫积弱的国情以及国库空虚的实际情况,执意隆重操办自己的60岁寿辰。自1888年便要求开始重修颐和园工程,所用木材皆需从南洋进口,开销巨大。慈禧在意的清漪园工程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都需要从国库拨款,李鸿章多次以“水师乃海防之根本”为拨款理由,与慈禧“抢”银子,这让慈禧对李鸿章颇有微词。身受慈禧提携之恩的张之洞明白慈禧对李鸿章的怒气与防备,并思考自己是否可以作为帮助慈禧牵制李鸿章的棋子?是否可以借此增强南洋派的实力进而与北洋派抗衡?只是这样的决定肯定会影响到铁厂的工作进展。
有种说法是:于公,可以说张之洞为了帮助慈禧牵制李鸿章和他的北洋集团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将铁厂建在了其极力反对的汉阳;于私,就纯属张之洞与李鸿章的个人恩怨与政治分歧了。出身世家,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教育,曾经是“清流派”要角的张之洞,虽说也是洋务运动的参与者与实施者,但始终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通俗来讲,就是在思想上还是要坚持中国传统的伦常经史,主要表现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上;至于西洋的东西,只有科技可以拿来使用,其他的一切都要屏蔽掉。所以他一方面积极学习西方的理学知识(数学、物理等),另一方面坚持在自己创办的学堂中沿用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讲授的也还是四书五经。简单来说,如果张之洞是一个穿着西洋燕尾服的中国人,那么李鸿章就是穿着长袍马褂的“西方人”,因而两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和政治思路不免出现差异。
当时的中国如果想要进步,改变国弱民贫的局面,仅仅向西方学习科技,模仿其工业生产是远远不够的。李鸿章认为,西方之所以先进,主要是因为其政治经济制度,科学技术是次要方面,所以中国应该参照西方进行制度改革,实行“全盘西化”。反之,张之洞始终无法认同并接受西方的价值体系,而且时刻对西方价值体系渗入中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这也是他与李鸿章无法共处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最根本原因[16]。结果就是,张之洞与李鸿章在政治上意见相左,在铁厂选址问题上更是存在分歧,并出现日益加剧的局面,致使二人的矛盾更加激化。虽说清政府指派张之洞督办铁厂,若铁厂建在李鸿章所极力主张的大冶,难保他之后不会插手铁厂事务,毕竟他当时的官职还是要绝对高于张之洞的。归根结底,张之洞为了避免铁厂的实际控制权旁落他人之手,从铁厂建立之初就表现出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谋求在气势上压倒对手。如此,张之洞便选定了武汉。毕竟在中国做事,不可能不考虑政治层面的因素。
洋务运动成功与否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企业创办成功与否也是如此。张之洞借着洋务运动的热潮以及自己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洞察力,顺利地在汉阳建立了中国第一家西式钢铁厂。在投产之前,看似“天时”与“地利”这两个因素都得以满足,那么决定汉阳铁厂成功与否的“人和”方面的因素又是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