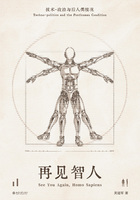
第8章 重思技术:作为“赛博格”的人类
“技术”早已是我们生活中的关键词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它有过充分的思考。2020年8月辞世的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在20世纪90年代便声称:“哲学在其起源处,并且直到今天,一直不把技术作为思想的对象。”[68]究竟什么是技术?这个问题实则并不容易回答。
在出版于2018年的《技术:一个概念的批判史》中,史学家埃里克·沙茨伯格提出,关于技术的定义始终一团混乱,“多元的含义彼此矛盾”,并在当代媒体知识分子乃至学者笔下变得越来越天花乱坠。沙氏特意指出,“一些学者将技术定义为‘事物事实上被做成和制成的所有方式’,这样的定义宽泛到几乎毫无用处,从炼钢到歌唱全都可以涵盖其中”[69]。
诚然,关于技术的界定一团混乱。然而在这团混乱里,沙茨伯格所单列出的“事物事实上被做成和制成的所有方式”,实际上并非是对理解技术“毫无用处”的定义——这个定义聚焦于从事物到人工制品(artifacts)的转化,而技术便是使这种转化发生的途径。这种理解,实则在“自然/文化”这个二元对立框架中,打开了两者变化(系一种单向变化)的通道:技术就是使事物从自然存在变成文化存在(文明存在)的那个力量。这个理解已然标识出了技术的文明性向度:技术创造出“后自然”的人工制品。这个观察进路,对于我们理解政治也同样有帮助(下一节详论)。
在这个理解之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对技术的思考。在散落于不同学科领域的一组学术著作中,我们可以追踪出对技术的另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器官的体外化”(ex-osomatization of organs)。这个理解,实则是从相反角度来切入对技术的思考:它并非聚焦于事物与人工制品的关联,而是聚焦于人工制品与人的关联。技术不只是使事物发生了变化(成为人工制品),也使人发生了变化(器官延展到了“体外”)。对技术的这个“器官学”理解,同样在“自然/文化”这个二元对立框架中,打开了两者变化(亦是一种单向变化)的通道——器官经过“体外化”,进入“后自然”的文化(文明)之域。
古希腊智者普罗塔戈拉讲述的关于埃庇米修斯兄弟的神话故事,值得在人工智能时代重访。诸神在创造诸种凡间生命(亦即必死生命)时,赋予了埃庇米修斯与普罗米修斯两兄弟一个任务,那就是分配相适应的能力以使它们能生存。埃庇米修斯把这个任务抢在手中,并说服其兄仅仅在旁监督:他给某种物种强壮,给另一些物种速度,给某些生物利爪、尖角或巨大体型,对未分配到这些的生物则授予其飞行或居于地下的能力……埃庇米修斯的唯一疏失在于,他彻底忘记了人类——他把所有能力全部分配出去后才发现,自己没有给人类留下任何能力。当埃庇米修斯束手无策时,普罗米修斯出手了——为补救其弟之失,他“从赫斐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偷来技术手艺(technical skill)以及火的使用(因为缺少火无人能获得或使用那技艺)并给予了人”[70]。
这可以说是关于技术的最有影响的神话故事之一,普罗米修斯也因此成为为人类“盗火”而遭受峻罚的悲剧英雄。此处值得提出的是,这个神话内嵌了关于技术的一种关键理解:埃庇米修斯给予各物种的,实则都是其器官所“自然”具有的能力;而普罗米修斯给予人类的,则恰恰是“后自然”的、非体内器官本身所具有的能力。这份能力,便是“技术”。对于技术,该神话没有聚焦在对事物的人工改造上,而是聚焦在人相对于其他物种的特殊性上。换言之,人和其他动物最根本的不同,便是人拥有“体外器官”。在这个聚焦视角下,技术便成为人的定义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换句话说,技术关涉“人类 起源”。
这也是斯蒂格勒三卷本《技术与时间》所坚持的观点,该著第一卷就题为《埃庇米修斯的过失》。从该神话出发,斯氏提出人是具有“原初缺失”的动物,处在“存在的缺省状态”;而人的“这种起源的缺省状态,被为其自身获取的诸种义肢、诸种工具所补充”[71]。技术所带来的,便正是义肢性的体外器官,斯氏称之为“技术存在”(technical beings)。在斯蒂格勒看来,在物理学所研究的无机存在(inorganic beings,非器官性存在)与生物学所研究的有机存在之间,恰恰存在着第三种类型:作为“无机的器官化存在”的技术存在。[72]
在斯蒂格勒这个论述基础上,值得进一步提出的是:技术存在既在无机存在与有机存在之间,又在两者之外。无机存在与有机存在,皆属于“自然”之域;而技术存在,则属于“后自然”之域,亦即,文化/文明之域。
早在1907年,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在其著作《创造性演化》中,已经区分出两种器官,生物器官与“人工器官”,并提出:“通过人工器官,自然的有机体被延展。”[73]柏氏进一步的论点是,这两种器官实则对应演化的两种方向:“本能”与“智能”。柏格森提出:“两者间的区别不是强度的区别,亦非更一般意义上度的区别,而是类的区别。”[74]“本能”生成体内器官;而“智能”则生成人工器官。
对于柏格森而言,智能才是人的根本性特征。他写道:
作为人之原初特征的智能,是制造人工对象(特别是制作工具的工具)的能力,并且是无止境地变更制造品的能力。[75]
换言之,在有机体(organism,即器官体)本身所具有的本能之外,人具有创造人工制品的智能(技术能力)。并且,智能始终在不断地、无上限地演化,从而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制品。柏格森把人工器官的演化,称为“创造性演化”。
在生物史学家、科学哲学家乔治·康吉莱姆看来,柏格森的《创造性演化》提出了一门“通用器官学”(general organol-ogy)。[76]生命的有机体演化(本能)与人的技术演化(智能),两者在“器官学”的视角下被统合起来(体内与体外器官),关联在一起进行研究。从器官学视角出发,康吉莱姆感叹:大量研究者用机器的结构与功能来解释有机体,却很少有人反过来用有机体的结构与功能来理解机器,“柏格森是非常少见的法国哲学家之一(如果不是唯一一位的话),把机械发明视作一个生物学功能,视作生命对物质的器官化的一个面向。”[77]
出自完全不同的学科背景,生物物理学家、数学家阿尔弗雷德·洛特卡亦实质性地呼应了柏格森。洛氏在1945年提出如下论点:人的独特性,就是在生物性演化(biological evolu-tion)之外发展出了“体外演化”(exosomatic evolution)。在洛特卡眼里,“人化”(hominization)就是体外化。[78]换言之,当器官开启体外演化那一刻,“人”就诞生了。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安德烈·勒罗伊 古汉把技术视作有机体与无机物之间的诸种“功能性挂钩”(functional couplings);而“人”就是生物世界加上技术的结果。勒氏写道:“手的自由,几乎必然隐含了一种不同于类人猿活动的技术活动。移动时自由的手,加上短脸、无尖齿,都指向了人工器官的使用,也就是工具的使用。”[79]
人工器官使用,同生物器官的演化交互触动:前者在创造性演化之同时,亦导致后者发生创造性演化。譬如,前肢不再参与移动而演化成“手”,而这又导致人的脸变短,不再主要靠脸部来进食和进攻。脸在“去功能化”之后,又“再功能化”出来表情以及言语。从通用器官学角度出发,我们就能研究两种类型器官在演化上的交互触动,尤其是人工器官(技术“智能”)对体内器官(生物“本能”)的一系列细微但深层的去功能化与再功能化改造。斯蒂格勒把拥有体外器官的生命称作“外有机体”(exorganism)。[80]这个生造概念暗示了,有机体在技术存在的义肢性加持下,变成了另外一种独特存在形式。
经由上述分析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提出如下这个充满“赛博朋克”气息的论题:人类就是“赛博格”(cyborg)。“赛博格”一词系曼菲德·克莱恩斯和内森·克莱恩于1960年提出的“控制论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一词的缩写,指有机体被嵌入生物机电部件后形成的“杂交物”。唐娜·哈拉维在其发表于1985年的《赛博格宣言》中,将“赛博格”视作打破“主体/对象”“自然/文化”“有机物/机器”“人/动物”这些二元对立框架的“边界混淆”。[81]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全新“杂交物”确实带来溢出20世纪文明地平线的思想冲击(以及视觉 想像冲击)。几十年后,当关于人工智能与基因工程的讨论猛然变成时代热潮后,“赛博格”又一次变成热词,构成了各类“超人类主义”与“后人类主义”画面中的一个关键意像。[82]
然而,不同于“仿生人”(android)或“生物机器人”(biorobot),“赛博格”尽管嵌有无机部件,但其思考动作均由有机体控制——那被植入的人工制品,主要是用以增加或强化有机体的能力。“赛博格”,显然就是一种“外有机体”。梯利·霍奎特精到地将“赛博格”的特征概括如下:“有机体突然被剥夺其自主,并变得依赖于技术。”[83]其实,恰恰从那一刻起,生命在生物性演化之外开启出了体外演化,并反过来影响生物性演化。当我们把技术存在理解为体外器官时,人类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已经是“赛博格”了。
故此,并非只有头部嵌有“脑机接口”才算是“赛博格”,在我们当下日常生活中,从衣服、眼镜到座驾,皆是有机体的“义肢”,用以强化其能力——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是彻头彻尾的“赛博格”。在安迪·克拉克看来,人便是“自然出生的赛博格”。[84]换句话说,“赛博格”不是“后人类”,而恰恰就是人。哈拉维曾宣称:“到了20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我们都是赛博格。”[85]实则,从人类起源时刻起,我们就是赛博格。
人类就是赛博格,亦即无机器官(cyb)与有机器官(org)的嵌合。彻底无机的人工智能,方可被视作妥当意义上的“后人类”。[86]而当人工智能以“脑机接口”等方式嵌入有机体后,这样的赛博格就变成超人类主义视域中的“超人类”了:作为人类之定义性特征的“智能”,被作为人工制品且能快速自我迭代的“人工智能”所叠加。[87]
柏格森把“智能”界定为生成人工器官的技术能力,而勒罗伊 古汉进一步把技术界定为有机体同外部环境的功能性挂钩。这对于我们界定人工智能的“智能”,是极具启发性的:人工智能(目下基于各种大数据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算法以及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大语言模型)之所以具有“智能”,正是因为它(a)能够在各面向上产生出全新的人工器官(如无人驾驶汽车),并且(b)高效率地达成特定功能。
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诚然可以被视作人类的技术智能之“增强版”。理论物理学家麦克斯·泰格马克在讨论“智能”时写道:“就‘什么是智能’,甚至连人工智能研究者们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泰氏本人对“智能”的定义是“完成复杂目标的能力”。[88]换言之,“智能”被定位为完成具体的目标导向性任务的能力。这同上述分析高度契合。
然而,身处人工智能在“智能”上正全面超过人类的当下时代,我们不得不反过来思考:有机体的“智人”(homo sa-piens)相对于人工智能能否堪称“有智”(sapiens)?这实是当代围绕人工智能所展开的讨论背后的最核心焦虑。
康吉莱姆在比较分析机器与有机体时提出,相对于技术智能的制品,有机体“具有更小的目标,和更大的潜能”。[89]那么,这份潜能除了康氏所说的“生命所包容的诸种怪物性”[90]外,还能在哪里去定位到?人(“智人”)从生物的怪物性中脱“颖”(聪慧)而出,除了技术的智能外,是否还有别的被实现了的潜能在发挥力量?
对于这组问题的思考,推动我们转到在今天学科体系下看似与技术彻底不相关的论域:政治。在其演化进程中,除了技术的智能外,人还依赖政治的智慧,而最终使自身从生物的怪物性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