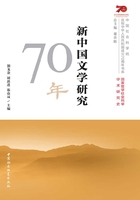
第三节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论选择
在讨论文化研究和现代性问题时,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声势与日俱增的“全球化背景”。2000年的《文学评论》,开辟了一个名为“全球化趋势中的文学与人”的专栏,先后发表了一批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生存与发展的研究文章。如涂险峰的《世纪交汇点上的问题意识与人文关怀》、昌切的《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汉语文学诉求的悖论》、樊星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选择》、南帆的《全球化与想象的可能》、肖鹰的《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胡明的《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学的现代性》、高小康的《文化冲突与文学“喧哗”》等,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
必须承认,“20世纪的历史上演到了最后一幕,全球化终于成为现实——甚至是不可抗拒的现实。信息、技术、商品、人员——尤其是货币资本正在全球范围空前频繁地往来,市场的开拓与扩张有力地突破国家、民族、文化风俗以及意识形态划出的传统疆域”[8]。南帆认为,从跨国公司、卫星电视、互联网络到麦当劳、奔驰汽车、卡通片,这些异国他乡的文化正在穿越巨大的空间距离和森严的国境线,越来越密集地植入本土。人们所栖身的空间已经与世界联为一体。东京的股市或者欧洲足球联赛并非一个区域性的事件,这些事件冲击波迅速地传遍地球的各个角落。“地球村”是历史为人类提供的下一个驿站。
全球化为文化带来了什么?有一种意见认为,诸多文化体系的交汇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文化的国际性“接轨”让人兴高采烈。种种跨国的文化盛会仿佛象征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秩序。但是,即使没有“后殖民”理论的武装,人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些文化体系之间的不平衡:好莱坞、迪斯科或者可口可乐的入侵面积远远超出了京剧、太极拳与茶文化的出口,国际互联网上的英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比较文学研究之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顽症,西装领带全面地征服了传统的长袍马褂……这些文化体系并非和睦地同舟共济,相反,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压迫、吞并与经济上的弱肉强食如出一辙,或者说,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与文化时常形成亲密的共谋,利润、民族国家、文明水平、价值信仰这些核心概念均是二者所共享的。对于某些幕僚出身的知识分子来说,与其温情脉脉地幻想全球文化的大联合,不如老谋深算地考虑这些文化体系之间水火不容的前景。
1997年,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在《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中说:“今天,人人都感到全球化已经达到了一个双曲线阶段。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可以确证它是一个独特的决定因素。”[9]他认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二、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引起了变革。三、旧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取代。四、文化研究迅速兴起。他的这些论断,与其说是对世界文学研究发展态势的一种预判,还不如说是对中国文论发展现状的综述。
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以不同的形式渗入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而隐于全球化背后的无疑是一种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主义。王宁认为,文化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抹去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差异,使其在同一个平面上显出趋同性特征;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过程中,我们所需要的是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作用,顺应国际潮流,与之沟通对话而非对立。黄鸣奋认为21世纪精通电脑的新型艺术家将大量涌现,网上艺术资源的空前丰富,新的艺术硬件、软件、载体的层出不穷,人类的生存方式(连同艺术形态)都将发生新的变革。“电脑艺术”将是电脑化的人类、智能动物和机器人所创造的艺术的总称。但也有人对“电脑艺术”表现出一种忧虑,即电脑艺术会不会因其数字化导致人的生存的游戏化,个人性走向交际功能的被消解、审美功能的被消解?[10]
全球化是人类传播和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毋庸讳言,学界有关“全球化”的看法往往是含混不清的,不同学者的观点充满差异与矛盾,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如有学者认为全球化使文艺创作的国际化合作成为家常便饭;文艺传播对于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依赖越来越明显;文艺的生产和加工将越来越多在“虚拟企业”中进行;跨文化传播而产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文艺活动的国家干预将越来越困难;网上文艺超越了国界,实现了空间上的“天涯若比邻”[11]。
但也有人认为,全球化有时成了最终解决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的终极幻想,“共有文明”的浪漫表述掩盖了“全球化”的问题;但有时我们又将全球化陌生化了,认为中国距现代化还十分遥远,简单地否定“全球化”的存在,或者用一种刻板的所谓“民粹”关切抗拒全球化。浪漫化和陌生化的两种倾向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封闭症。[12]而这种“思想封闭症”与文化殖民主义的甚嚣尘上多少有些牵连。
更多人则认为文化全球化并不可怕,它也许会给我们带来21世纪的东西方文化共处和对话的新局面。文化全球化并非像经济全球化那样使各民族的文化走向同一性,而有可能从另一个方面保持不同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平等地位,通过全球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理论对话而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文化研究并非必须与文学研究呈截然对立的态势,文化研究中的不少命题来自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因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将传统的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是有利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互补的一种选择。此外,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课题也有助于对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领域内无法解答的问题提供解决的办法,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将文学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下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经济与科技全球化已成不可阻挡之势,无孔不入的资本与信息如水银泻地,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地球村”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文化、文艺全球化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始终受到人文学者的怀疑,不少学者认为,不能把全球化概念随心所欲地扩大到精神与文化领域。因为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只能是一个互动的历史过程。乐黛云认为世纪之交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消长的时代。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要保持文化多元和文化个性,保持学术个性不是很容易的。因此,她觉得要同两条路线作斗争:一是反对全球文化霸权主义,二是反对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西方文化圈子里现在有一种相互融合相互接纳的趋向,所以她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文论,就应该展现中国文学理论自己的个性,在参与世界文论的对话中寻找发展机遇。[13]
有一种意见认为,20世纪曾经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外来文论输入中国。而每一次的性质、特点与方向不尽相同。“五四”时期是20世纪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来文论输入,主要特点是从近代欧洲文论逐渐转向俄苏文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外来文论输入。这一次是在“全面学习苏联”“一边倒”的特殊时代氛围中进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资源及学术动态,则完全未能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新时期以来,在中国大举登陆的西方文论产生了强大震撼力与冲击波。
概而言之,20世纪西方现代文论的输入,较好地体现了中国文论发展的全球化大融合趋势和坚守民族特色的主观意愿。“大胆拿来”,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思想资源,使我们置身于世界文论格局之中,和世界文论的发展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与世界文论主潮保持同步思考,并对其挑战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应。这大大扩大了我们的理论视野,拓展了我们的思维空间,为我们的文艺理论的发展打开了一片新的天空,改变了我国文论的面貌。事实上,西方文论的输入,已经成为推动中国近百年文论发展的有力杠杆之一。[14]但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大胆拿来”的同时,如何“坚守本来”“开创未来”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理论难题。
[1] 高建平:《新时期文艺学20年》,《文艺争鸣》1998年第4期。
[2] 叶舒宪:《“文化”概念的破学科效应》,《中外文化与文论》1998年第1期。
[3] 李凤亮:《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暨南学报》1998年第 3期。
[4] 王岳川:《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 4期。
[5] 陈晓明:《文化研究: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载荣长海编《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6] 钱中文:《文艺理论现代性的两个问题》,《文学论集》第11辑(2000年卷)。
[7] 徐新建、阎嘉:《面对现实、融汇中西》,《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8] 南帆:《全球化与想象的可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9]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王逢振译,《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10] 郦因素:《文学理论:留给二十一世纪的话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11] 黄鸣奋:《全球化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文艺报》1998年11月2日。
[12] 张颐武:《全球化的文化挑战》,《文艺争鸣》1999年第4期。
[13] 乐黛云:《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化多元化》,《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4] 代迅:《全球视野中的本土化选择:近百年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