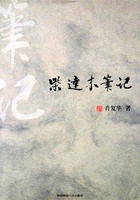
最后的老基地
汽车沿着当金山崖的河谷逆流而上,雪水泛着白沫拍击着乱石扬起雪白的浪花,山石顽强地坚定着自己的立场;浪花歌唱着自由的欢畅;浪花涟涟,那就是天上的雪花赠与当金山的一条洁白的项链。沿着这条天然项链,汽车下山了,当金山过去了,我们过来了,眼前的柴达木豁然开朗,大小苏干湖如那项链垂落下的蓝宝石坠儿,安详地袒露在柴达木浩瀚的胸襟上,泛着绿的翡翠、闪着银的锃亮、吐着金的阳光。
司机冯国斌师傅说,昨夜当金山和冷湖都下了大雨,真是柴达木千载难逢的好天气!同行的贾兰英立刻感慨道:“柴达木知道我们回来了,才用这么珍贵的礼物迎接我们。是啊,上帝永不背弃永远热爱他的人。冷湖的年蒸发量为降雨量的100倍。四十年前,在我们只有泪、没有雨的日子里,我们无怨;在我们只有汗、没有雨的日子里,我们无悔。四十年了,我们依然那么热爱着你——我们青春时的家。天感动了,雨就会爱人。
能望见冷湖了,那是1954年新中国第一支勘探队来此时,那湖水冷的能“咬手”而得名。与冷湖遥相呼应的是赛时腾山,不知哪年哪月祁连山火山爆发,大山内蕴含的精液与骨髓喷薄而出这火筑成的赛时腾山。我们一帮北京学生曾徒步一天去赛时腾山探险,师傅说:“望山跑死马,在戈壁大漠一旦迷路,可就‘古来白骨无人收’啦!”
那时青春的我们并不明白青春。那时的青春是什么,那时的青春就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天不怕地不怕,风雪雷电任随它”。正青春的我们问师傅,那山为什么叫赛时腾?师傅说:“那是蒙语,大概是‘黑色石头’的意思。四十年来,我们便一直把它叫:黑石头山。”直到这次来,我们才寻到正确答案:“赛时腾”汉语为“苏醒”之意。
然而沉睡千万年的赛时腾真正苏醒,应是那口“美名天下扬”的“英雄地中”井日喷原油800吨的1957年。诗人李季二进柴达木时,曾写下《一听冷湖喷了油》的诗歌:一听冷湖喷了油,柴达木盆地闹翻天……作家李若冰同年写下散文《冷湖的星塔》:谁只要来到柴达木盆地,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们的去处……

图为作者感叹“真的老去了”的老基地
如今的冷湖呢?当汽车驶进冷湖老基地时,眼前是一片片断壁残垣的废墟,当年作为勘探开发石油的物资、运输、机修辅助生产保障的老基地老了,沉寂了,睡去了。老基地的梦只能寄存在冷湖那被风吹动不停的褶皱里,取而代之的是隔山相望的敦煌新基地。这是一个时代更替另一个时代的使然?我们这帮人,刚离开了敦煌基地的“新颜”,竟忘情地一头扑向老基地的“旧貌”,是企图在这一片废墟上拾遗回我们青春花季时的花蕊吗?或者说,在这片废墟里曾埋藏着一种什么样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奇在召唤着我们。车未停稳,曾在运输处当过副处长的黄溥就迫不及待地跳下车,一脚踩进一个雨后积水的大坑里,他也来不及跺跺脚、擦擦泥便指着眼前的废墟说:“这儿就是咱们的大礼堂。”这是老基地唯一一个二层楼的大礼堂。这里曾是我们演过样板戏、唱过语录歌、跳过忠字舞的唯一“文化活动”场所。邓永华和李秀荣两人不由顿生感慨:“记得1971年我们刚参加工作不久时,每天下班去黑石山凿山拉石头,每个班拉五车,那么大的石头,真搬不动,累死了,累的骨头疼,晚上都睡不着觉。”如今,让她们睡不着觉的大礼堂寿终正寝了。
我独自穿过大礼堂走进废墟,木然地望着远处的冷湖和湖畔的那片墓地。他们是搬不走了,那里有我们的同学,他们叫:吴长江、周祖宏。我们都想去看看他们,可司机说,雨太大,车过不去了。天苍苍,野茫茫,何处话凄凉。突然我发现不远处有一顶帐篷冒着炊烟,在这片废墟里居然还有生的气息。
帐篷里,黑漆漆地坐着两个中年汉子,一个和面、一个择菜。
“中午吃什么呀?拉条子还是尕面片?”一进帐篷我就用西北话打招呼,以消除他们在这荒郊野外对陌生人的警惕感。
“拉条子。”果然,他们也热情地开始和我对话。
“你们这吃的喝的从哪来呀?”
“老板从敦煌送来。”
“这黑灯瞎火的没电啊。”
“喏,”和面的汉子努努嘴,“有马灯。”
“你们跑到这狼都不来的鬼地方干什么呀?”
“唉,人都搬走了,狼就来了。喏,山那边,喏,湖那边,来得多。”
“不怕么?”
“不怕,我们人多,六个。还有马灯,狼怕光。”
后来我知道这六人有两对夫妻带着两个亲戚,在这片废墟里捡完整的砖,一块可卖一毛钱,他们正月十八上来的,已干了半年多了,还没回过家。他们都是从甘肃山丹来的农民,穷啊,于是先富起来的人便把他们引到这儿“致富”。老板说这里的砖烧得质量好,瓷实,到工地受欢迎,卖得好。是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石油工人自己烧的砖没有“豆腐渣”,因为我们是自己给自己盖房子。我挺得意地走了。

图为作者与拾到照片等待照片主人的赵玉英
走出了老远,感觉身后有人喊我“师傅、师傅……”她那太地道的甘肃土话我听不懂,依然径自走去。她终于气喘吁吁地追上了我,“师傅,你是这里的人吗?”我说是,在这里待了二十多年呢。她赶紧问:“喏,你认识么?”
她的举动让我一下充满好奇,那是一家老少三代的全家福,可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好奇地问她:“这照片你从哪弄来的?”
“喏,”她手指着远处的一片废墟,“就在那一片砖块下埋着,还有一个书包、五六张照片,你要是认识,就送还给人家。”
我被她的精神感动了,拉着她说:“走,那边车里有一个曾在这里当过头儿的或许认识。”
路上我知道她叫赵玉英,我把她的名字写在采访本上问道:“是这三个字吗?”她摇摇头说不识字,好像是。四十一岁的她和丈夫来这里捡砖,为给大女儿和小儿子挣学费。

图为作者一直惦念寻找的老基地的一家人
真可惜,黄溥及全车的人都说不认识照片上的人。我想了想说:“你把照片给我吧,我帮你找。”
谁知她摇摇头说:“你们走了不知啥时再来,我一直在这儿捡砖,能上这个地儿来的人,一定在这儿过过日子,他们一定会有认识的。来人,我就会去问的。”
被感动的黄溥跳下车说:“这样吧,我把照片翻拍下来,我们大家帮你一起找。”
她的脸上一下充满了灿烂的笑容连声说:“谢谢你们。”
我握住她的手说:“该谢的是你啊!来,我们一起照张相留个纪念吧!”她把照片郑重地捧在胸前,那一刻的她,一脸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