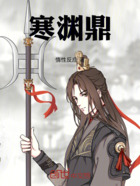
第6章 龙纛下的棋局
后金军大营,中军王帐。
帐外,寒风卷着雪沫,抽打着巨大的织金龙纛,发出猎猎的声响,如同无数冤魂在呜咽。帐内,却是另一番天地。暖意融融,巨大的铜盆里,上好的银霜炭无声燃烧,散发出松木的清香,与帐外弥漫的血腥和焦糊味形成刺鼻的对比。地上铺着厚厚的、色彩斑斓的波斯地毯,踩上去柔软无声。帐壁悬挂着斑斓的虎皮和熊罴之属,彰显着主人的勇武与征服。
皇太极斜倚在一张铺着整张白虎皮的宽大坐榻上。他并未着甲,一身深紫色绣金团龙常服,外罩一件玄狐皮大氅,衬得他原本就宽厚的肩膀更加沉稳。他面容方正,肤色微深,下颌蓄着精心修剪的短须,眼神沉静,仿佛深潭之水,不起波澜。此刻,他正用小银刀慢条斯理地削着一颗冻梨,动作优雅从容,与帐外炼狱般的战场形成了诡异而强烈的反差。
李轩被两名身披重甲、如同铁塔般的巴牙喇(护军)押着,站在帐中。沉重的木枷和铁链尚未除去,冰冷的金属硌着他的皮肉,长时间的束缚让他的双臂几乎失去知觉,脖颈更是僵硬酸痛。他强迫自己站直身体,目光平静地迎向那位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后金之主。
“明狗,跪下!”押解他进来的那名脸上带着狰狞刀疤的拔什库(十夫长),见李轩竟敢直视大汗,厉声呵斥,抬脚就要踹向李轩的膝弯。
“巴图鲁。”皇太极削梨的手微微一顿,头也没抬,只淡淡吐出三个字。
那拔什库巴图鲁如同被施了定身法,踹到一半的脚硬生生停在半空,脸上凶悍之色瞬间化为惶恐,躬身退到一旁,大气不敢出。
帐内一片死寂,只剩下银刀划过冻梨那细微的沙沙声。良久,皇太极才将削好的一片晶莹梨肉送入口中,慢慢咀嚼,仿佛在品味世间至美。他咽下梨肉,拿起一方雪白的丝帕,仔细擦了擦手,这才抬起眼,目光第一次真正落在李轩身上。
那目光并不如何锐利逼人,却像深秋的潭水,带着一种能穿透骨髓的冰冷与审视。它缓缓扫过李轩洗得发白、沾满泥污和雪沫的青布囚服,扫过他脖颈上沉重的木枷和手腕脚踝上粗粝的铁链,最后,定格在他那双眼睛上。那双眼睛,没有预想中的恐惧、谄媚或愤怒,只有一种近乎疲惫的沉静,以及沉静之下,难以窥探的深潭。
“李轩?”皇太极开口了,声音不高,带着一种奇特的、混合着关外口音的沉稳汉话,“归德府的书生?被崇祯皇帝锁拿进京的钦犯?”他语气平淡,仿佛在陈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说你有绝密军情,要面见于我?现在,你见到了。说。”
每一个字都清晰沉稳,却带着无形的重压。帐内侍立的范文程等文臣,以及多尔衮、阿济格等悍将,目光都聚焦在李轩身上,如同群狼环伺。
李轩感到喉咙干涩,冰冷的铁链摩擦着伤口,带来阵阵刺痛。他深吸一口气,压下身体的疲惫和不适,迎着皇太极那深潭般的目光,声音因干渴而沙哑,却努力保持着平稳:
“大汗明鉴。在下李轩,一介书生,因在归德推广活命粮种,触怒地方豪强,遭其构陷,被朝廷锁拿。所谓绝密军情,”他微微一顿,眼神坦荡,“实乃在下脱身保命的权宜之计。若直言相告,恐怕未及面见大汗,便已身首异处于游骑刀下。”
此言一出,帐内气氛瞬间凝固!多尔衮眼中厉芒一闪,阿济格更是按住了腰刀刀柄,脸上露出被戏耍的暴怒。范文程则微微蹙眉,若有所思。那拔什库巴图鲁更是气得脸膛发紫,若非皇太极在前,恐怕早已拔刀相向。
皇太极脸上的肌肉似乎没有任何抽动,只是那双深潭般的眸子,微微眯了一下,像平静的水面投入了一颗石子,荡开一圈极细微的涟漪。他没有立刻发作,只是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坐榻白虎皮光滑的皮毛,声音依旧听不出喜怒:
“哦?权宜之计?”他微微向前倾身,一股无形的压迫感瞬间笼罩了李轩,“那你可知,欺骗本汗,会是什么下场?剥皮?点天灯?还是……喂狗?”
每一个词,都带着血腥的寒意。帐内的温度仿佛骤然下降。
李轩感觉背脊的寒意直冲头顶,但他知道自己已无退路。他挺直了因枷锁而佝偻的脊背,目光毫不避让:“在下深知死罪。然,蝼蚁尚且贪生。在下所言虽非军情,但于大汗,或比十万军情更有价值。”
“更有价值?”皇太极嘴角似乎勾起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弧度,是嘲讽,也是兴味,“说来听听。若说不出个所以然,本汗会让你明白,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李轩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撞击着冰冷的枷锁。他强迫自己冷静,大脑飞速运转,将早已准备好的腹稿,结合眼前这深不可测的对手,重新组织。
“其一,价值在‘知’。”李轩的声音清晰起来,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冷静,“大汗雄才大略,志在天下。然欲取天下,必先知天下。大汗可知,此刻大明朝廷中枢,是何景象?”
他顿了顿,不给皇太极打断的机会,语速加快:“崇祯帝登基五载,诛除阉党,看似励精图治,实则刚愎多疑,刻薄寡恩!朝中党争酷烈,东林清流与阉党余孽势同水火,互相倾轧,视国事如儿戏!地方官员,贪墨成风,盘剥无度,视百姓如草芥!天灾频仍,流寇四起,民怨沸腾,已如遍地干柴!此非在下妄言,乃我亲身经历,归德府豪强朱仁富,囤积居奇,欲置万千饥民于死地,官府视若无睹,反助其构陷于我!此等朝廷,此等官吏,根基早已腐朽透顶!大汗兵锋所指,破其门户易,收其民心……难!”
他直视着皇太极的眼睛,一字一句:“大汗可知,为何山海关能如此轻易被您攻破?非关将士不勇,非关孙传庭无能!实乃朝廷党争掣肘,粮饷不济,军心涣散,更有奸细内应!此乃大明心腹之疾,亦是您最大的敌人——非在关外,而在其庙堂之内!”
帐内一片寂静。范文程眼中精光闪动,微微颔首。多尔衮、阿济格等悍将虽对汉人文辞不甚了了,却也听出了李轩话中对明朝的深刻剖析和贬斥,脸上怒色稍霁。
皇太极依旧面无表情,只是摩挲虎皮的手指停了下来。他身体微微后靠,靠在白虎皮的软垫上,似乎在消化李轩的话。
“其二,”李轩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嘶哑,但气势不减,“价值在‘器’!大汗铁骑,天下无双。然攻城拔寨,攻坚克锐,火器之利,不可或缺。大汗军中红夷大炮,威力惊人,然……”他话锋一转,“射速缓慢,移动笨拙,且需精熟炮手操持。此等利器,大明亦有,且更多!孙传庭守山海关,必倚仗此物!大汗可知其布防?可知其弱点?可知其火药配比与射程之秘?在下虽不知具体军情,然饱读杂书,于火器一道,略知一二。譬如,红夷大炮最惧者,非刀剑,乃泥泞潮湿!炮管过热易炸,需以湿布包裹降温,然湿气侵入药室,则哑火频发……”
他侃侃而谈,将后世所知的一些关于早期火器(尤其是前膛装填的重型火炮)的常识性弱点,结合这个时代的实际情况,半真半假地抛了出来。这些知识,对于皇太极麾下已初步掌握火器、并深知其威力的将领谋臣来说,无异于黑暗中点亮的一盏灯!阿济格甚至忍不住向前踏了半步。
皇太极的目光,终于起了变化。那深潭般的眼底,掠过一丝真正的、带着审视与估量的光芒。他不再将李轩仅仅视为一个狡辩的囚徒,更像是在打量一件……或许有用的工具。
“其三,”李轩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价值在‘势’!大汗今日破关,威震华夏。然,破关易,守土难,收民心更难!大明虽朽,然其立国二百余载,纲常名教,深入人心。大汗若一味恃强,杀戮过甚,则汉人畏威而不怀德,反抗必如野火,此起彼伏!归德之事,便是一例!朱仁富死,非死于我手,死于天怒人怨!在下推广新粮,非为邀名,实为活命!百姓所求,不过一饭一衣,一隅安身!大汗欲取中原,必先解民倒悬!效仿古之圣王,行屯田,减赋税,安流民,用汉官,施仁政!如此,方能使汉人知大汗非为劫掠之酋长,实乃拯民于水火之真命!”
“真命?”皇太极轻轻重复了这两个字,嘴角那抹若有若无的弧度似乎深了一分。他缓缓站起身,高大的身影在帐内灯火的映照下投下巨大的阴影,几乎将李轩完全笼罩。他踱步到李轩面前,两人距离不过数尺。皇太极的目光如同实质的探针,再次深深刺入李轩的眼底,仿佛要将他灵魂深处的一切都挖掘出来。
“好一番慷慨陈词!知庙堂之弊,晓火器之秘,更懂收拢人心之道。”皇太极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洞悉人心的力量,“李轩,你告诉本汗,你究竟是何人?一介书生,焉能有此见识?焉能有此胆魄,在本汗面前侃侃而谈,指点江山?你所谓的‘权宜之计’,恐怕也只是你更大棋局中的一步吧?你……究竟想从本汗这里,得到什么?”
空气瞬间绷紧,如同拉满的弓弦!皇太极的问题,直指核心,剥开了所有华丽的辞藻和看似合理的分析,露出了赤裸裸的动机疑云。多尔衮的手再次按上了刀柄,范文程屏住了呼吸。
李轩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几乎要将他压垮。皇太极的敏锐和直接,远超他的预判。他不能退缩,不能犹豫,任何一丝迟疑,都可能被解读为心虚。
他迎着那几乎能将他灵魂洞穿的目光,脸上露出一抹极其复杂的神色——混杂着坦诚、无奈,以及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破罐破摔。
“大汗明察秋毫。”李轩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的沙哑,“在下所求,不过‘活命’二字。大明朝廷视我为妖人、为叛逆,锁拿进京,必死无疑!投奔大汗,或许尚有一线生机。至于见识胆魄……乱世求生,蝼蚁亦需挣扎。在下所言,不过是将所见所闻所思,和盘托出,以证己身非无用之辈,或可……在大汗帐下,求一容身之地,苟全性命于乱世罢了。”他微微垂下眼帘,浓密的睫毛在苍白的脸上投下小片阴影,掩去了眸底深处一闪而过的精光。示弱,有时是最好的铠甲。
“容身之地?”皇太极的目光在李轩低垂的脸上逡巡着,仿佛在掂量他话语中的真伪。帐内静得可怕,只有炭火偶尔发出的轻微噼啪声。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拉长、凝固。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即将达到顶点时,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伴随着盔甲甲叶碰撞的哗啦声!一名浑身浴血、甲胄上布满刀痕箭孔的戈什哈(传令兵),未经通报便猛地掀开厚重的帐帘闯入,带进一股刺骨的寒风和浓烈的血腥气!
“报——!”戈什哈单膝跪地,声音嘶哑急促,带着巨大的惊惶,“启禀大汗!明军残部据守内城街巷,负隅顽抗!孙传庭老贼……孙传庭老贼亲率死士,点燃了靠近内城水门秘道附近的火药库!引发大爆炸!我军……我军冲击内城的前锋牛录损失惨重!阿巴泰贝子……阿巴泰贝子身陷火海,生死不明!”
“什么?!”帐内瞬间炸开!多尔衮、阿济格等悍将勃然变色!范文程也惊得站了起来!
皇太极猛地转身,脸上那古井无波的沉静第一次被打破,眉头骤然锁紧,眼中爆射出骇人的寒光!一股凛冽的杀意如同实质般弥漫开来!
李轩心中亦是巨震!孙传庭!他果然还没死!而且,竟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再次狠狠咬了皇太极一口!
皇太极的目光,如同两道冰冷的闪电,倏然扫过帐内诸将,最后,竟又落回了李轩身上!那眼神极其复杂,有被孙传庭顽强抵抗激起的暴怒,有对阿巴泰生死的担忧,更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审视!仿佛在问:你方才所言大明腐朽、军心涣散,那这孙传庭和这些死战不退的明军,又作何解?
李轩心头一紧,知道这是最危险的时刻!任何对孙传庭的贬低或对明军抵抗的轻描淡写,都只会引起皇太极更深的猜忌和厌恶!他必须给出一个能自圆其说、又能触动这位枭雄内心的解释!
他深吸一口气,迎着皇太极那冰火交织的目光,抢在其他人开口前,用一种带着沉重与敬意的语气,清晰地说道:
“孙督师……真国士也!大明有此忠勇,乃其国祚未尽之证!然……”他话锋一转,语气带着一种洞察世事的悲凉,“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孙督师之忠勇,恰恰映照出大明朝廷之昏聩!如此良将,若得明主信重,粮饷充足,将士用命,山海关何至于此?大明何至于此?孙督师今日之血战,非为崇祯,非为那腐朽的朝廷,乃是为其心中之道义,为身后之黎庶!此等人物,可敬,可叹,然……亦可悲!”
李轩的话,像一盆冰水,浇在帐内因阿巴泰噩耗而升腾的怒火上。他既肯定了孙传庭的忠勇(这符合皇太极自身对勇士的价值观),又将其悲壮结局归咎于明朝的腐朽(这契合皇太极的战略认知),更点出了其精神内核(为道义和黎庶),无形中拔高了孙传庭的形象,也巧妙地将皇太极的怒火引向了明朝朝廷本身,而非孙传庭个人。
皇太极眼中的暴怒和杀意,在李轩这番话语中,如同被投入石子的水面,剧烈地波动了一下,竟奇异地平复了几分。他深深看了李轩一眼,那目光中的审视意味更加浓厚,仿佛要重新评估眼前这个囚徒的价值。
“传令!”皇太极猛地转身,不再看李轩,声音恢复了惯常的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命多尔衮、阿济格,亲率两黄旗精锐,不计代价,给本汗碾碎内城残敌!活要见孙传庭,死……也要见尸!务必找到水门秘道入口!阿巴泰……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他顿了顿,补充道,“传令各部,约束士卒,入城后,非激烈抵抗者,不得滥杀!尤其……不得惊扰粮仓、匠户!”
“嗻!”多尔衮、阿济格等将轰然应诺,杀气腾腾地冲出大帐。
帐内只剩下皇太极、范文程、几名侍卫,以及依旧被枷锁禁锢的李轩。气氛再次变得微妙而凝重。
皇太极缓缓踱步,走回白虎皮坐榻,却没有立刻坐下。他背对着李轩,高大的身影在灯火下显得有些沉默。良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听不出情绪:
“李先生。”他用了“先生”这个称谓,而非之前的“明狗”或直呼其名,“你方才所言,关于火器弱点,关于民心……很有意思。把你所知的,关于红夷大炮、火铳,以及……你所推广的那种耐旱高产粮种的一切,”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详详细细,写下来。”
他挥了挥手,一名侍卫立刻上前,粗暴地卸下了李轩脖颈上的木枷,但手脚的铁链并未除去。另一名侍卫则捧来一张矮几,上面铺着粗糙的毛边纸,放着一支炭笔和一块劣质的墨锭。
“就在这里写。”皇太极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写清楚,写明白。本汗……要看你的诚意。”他重新坐回榻上,闭目养神,不再看李轩。但李轩知道,那双看似闭合的眼睛背后,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如同鹰隼般的监视。
沉重的枷锁卸去,脖颈骤然一松,带来一阵眩晕般的轻松感,随即是更加尖锐的酸痛。李轩活动了一下几乎僵硬的脖子,目光落在矮几上粗糙的纸张和炭笔上。冰冷的铁链缠绕着手腕脚踝,每一次细微的动作都带来金属摩擦的刺痛和冰冷的触感。
他缓缓坐下,拿起那块冰冷的炭笔。粗糙的笔尖划过毛边纸,发出沙沙的声响。他没有立刻写下那些足以改变战争进程的火器机密,而是深吸一口气,提笔在纸页最上方,用炭笔写下了两个方正有力、在这个时代却显得极其突兀的简体字:
土豆
红薯
这两个字,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瞬间吸引了帐内所有人的目光。范文程眼中闪过一丝惊异,侍卫们则一脸茫然。连闭目养神的皇太极,似乎也微微动了一下眼皮。
李轩没有停顿,开始在“土豆”二字下方,详细写下其特性:耐旱耐瘠,不挑土壤,亩产极高,块茎可食,生长期短……笔迹沉稳,条理清晰。他故意放慢了速度,每一个字都写得一丝不苟,仿佛在精心雕琢。他在拖延时间,也在整理思绪,更是在观察。观察皇太极的反应,观察这帐内微妙的气氛变化。
写完土豆,他又在“红薯”下方同样列明其优点。然后,才在纸张的下方空白处,另起一行,开始书写关于火器的内容。他没有直接写红夷大炮的致命弱点,而是先写了一些关于火药配比、颗粒大小对燃烧效率和射程影响的常识性知识,这些都是这个时代顶尖火器专家或许也知晓,但普通将领绝对不了解的细节。他写得条分缕析,如同在撰写一份严谨的教材。
“火硝提纯之法,以水溶之,反复熬煮结晶,可得精硝,威力倍增……”
“火药颗粒,并非越细越好,需大小均匀,以指捻不碎为佳,如此燃烧更匀,不易炸膛……”
“鸟铳(火绳枪)引火药池,需常保干燥,湿气侵入则哑火频发,可用油布覆盖……”
他写得很慢,很细。时间在沙沙的书写声中悄然流逝。帐外,隐隐传来更加激烈、更加绝望的喊杀声和爆炸声,那是多尔衮和阿济格正在对山海关内城残存的明军发动最后的、也是最残酷的进攻。每一次巨大的爆炸声传来,都让帐内的空气为之凝固,侍卫们的呼吸会下意识地屏住,皇太极搭在膝盖上的手指,也会微不可察地收紧一下。
李轩的心,也随着那远方的厮杀声而揪紧。孙传庭……还能撑多久?那份血书……能送到京城吗?崇祯……会做出什么决定?他笔下未停,心中却如同翻江倒海。他深知,自己此刻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加速孙传庭和那些残存明军的死亡,也可能为未来无数汉人百姓带来难以预料的灾祸。然而,为了活命,为了能继续下这盘以天下为棋局的险棋,他别无选择。他只能赌,赌皇太极对知识的重视,赌自己后续的价值,能压过眼前这份“投名状”带来的道德负罪感。
终于,在写到关于红夷大炮炮管过热需要降温、但湿气侵入药室会引发更大风险这一关键点时,李轩停下了笔。他放下炭笔,活动了一下因长时间书写而酸痛僵硬的手指。粗糙的纸张上,已密密麻麻写满了炭黑色的字迹。
他抬起头,看向皇太极。后者不知何时已睁开了眼睛,正静静地看着他,或者说,看着他面前那张写满了字的纸。那目光,深邃依旧,却似乎少了几分最初的冰冷审视,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是满意?是探究?还是更深的算计?
“大汗。”李轩的声音带着书写后的干涩,“此乃在下所知之概要。火器之道,深奥繁杂,非一日之功。粮种之事,更需实地试种,方知成效。纸上谈兵,终觉浅薄。”
皇太极没有说话,只是对范文程使了个眼色。范文程立刻上前,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张还带着炭笔粉末气息的纸张,如同捧着一件稀世珍宝。他快速扫视着上面的内容,越看,眼中惊异之色越浓,随即化为凝重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他对着皇太极,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
皇太极的目光再次落回李轩身上,停留了片刻。那片刻的凝视,仿佛有千钧之重。李轩坦然迎视,眼神中带着疲惫,带着无奈,也带着一丝等待裁决的平静。
“送李先生去休息。”皇太极终于开口,声音恢复了惯常的沉稳,听不出任何情绪,“好生看管。没有本汗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接近打扰。”他顿了顿,补充道,“饮食……按幕僚标准供给。”
“嗻!”侍卫应声上前。
李轩心中一块巨石轰然落地,紧绷的神经骤然松弛,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巨大的、几乎将他淹没的疲惫感。他站起身,沉重的铁链哗啦作响。在两名侍卫的“护送”下,他转身,步履有些蹒跚地走向帐口。掀开厚重帐帘的刹那,一股夹杂着浓烈血腥、硝烟和焦糊味的寒风猛地灌入,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
帐外,天色更加阴沉,风雪似乎更大了。远处山海关内城方向,火光冲天,映红了半边铅灰色的苍穹,厮杀声、爆炸声如同地狱的丧钟,依旧隐隐传来。那火光,映在李轩深不见底的眼眸里,跳跃着,燃烧着。
他知道,自己暂时活下来了。用一些知识,换来了片刻喘息。但他也踏入了更深、更危险的漩涡。皇太极的“幕僚标准”,既是恩赏,也是枷锁。这后金大营,是新的囚笼,也是新的棋盘。而山海关的血火,京城的暗流,才是这盘大棋真正的开局。他回头,最后看了一眼那在风雪中猎猎作响的织金龙纛,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漫天风雪之中,走向那个未知的、由重兵把守的营帐。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风雪与营帐的阴影里,只留下那顶巨大的王帐,在关外的寒风中,如同沉默的巨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