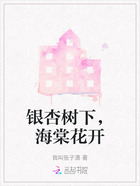
第2章 红妆别离
1906年农历三月初八,宜嫁娶。
天还没亮,金府就已经灯火通明。丫鬟仆妇们穿梭如织,为即将出嫁的大小姐做最后的准备。
金道凤坐在梳妆台前,像个精致的木偶般任由全福夫人为她梳妆。全福夫人一边梳头一边唱着吉祥话:“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
铜镜中,金道凤看到自己苍白的脸被涂上胭脂,点染得如同画中人。头上沉重的凤冠压得她脖子发酸,大红嫁衣上金线绣的凤凰在烛光下熠熠生辉。
“小姐今天真美。“贴身丫鬟春桃在一旁抹眼泪。
金道凤勉强笑了笑,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门口。从早上起,她就没见到道友。按照习俗,弟弟应该来给她送嫁,可直到现在,那个熟悉的身影都没有出现。
“春桃,道友呢?“她终于忍不住问道。
春桃面露难色:“少爷他...一早就不见人影,老爷派人找遍了府里也没找到。“
金道凤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她知道弟弟反对这门婚事,却没想到他会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闹脾气。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涌上心头,连带着对即将到来的婚礼也生出了几分抗拒。
“新娘子准备好了吗?吉时快到了!“喜娘在门外高声问道。
金夫人匆匆进来,看到盛装的女儿,眼眶顿时红了:“我的儿...“话未说完便哽咽起来。
金道凤握住母亲的手:“母亲别难过,程家离得不远,女儿会常回来看您的。“
金夫人擦了擦眼泪,从怀中取出一个锦盒:“这是母亲当年的嫁妆,现在传给你。“盒中是一对晶莹剔透的翡翠玉镯,“记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娘家永远是你的后盾。“
金道凤郑重地接过玉镯,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在脸颊上冲出两道脂粉的痕迹。喜娘连忙上前补妆:“新娘子可不能哭,不吉利!“
外面鞭炮声骤响,鼓乐齐鸣。“迎亲的队伍到了!“有人高声喊道。
金道凤被盖上大红盖头,在众人的搀扶下向外走去。眼前只剩一片血红,耳边充斥着喧闹的喜乐和祝福声。她感觉自己像一叶小舟,被命运的浪潮推着向前,无法回头。
迈出金府大门的那一刻,她突然听到一声熟悉的呼唤:“姐姐!“
盖头下的金道凤浑身一震,下意识想掀开盖头,却被喜娘拦住:“新娘子可不能自己掀盖头!“
“道友?是你吗?“她急切地问道。
没有回答。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接着是金鸿煊压低的呵斥声。金道凤被半扶半抱地送上了花轿,在轿帘落下前的最后一瞬,她似乎瞥见人群后方,道友站在远处的一棵老槐树下,脸上带着她从未见过的悲伤表情。
轿子起程了。金道凤终于忍不住掀开盖头一角,透过轿窗回望金府大门。她看到父亲严肃的面容,母亲抹泪的身影,还有——道友追着轿子跑了几步,然后停下来,像个迷路的孩子般站在原地,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在拐角处。
一滴泪落在嫁衣上,晕开一朵暗红的花。
---
程家的婚礼排场比金家想象的还要大。作为北洋新贵的程家,婚礼既保留了传统仪式,又融入了不少西洋元素。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都到场了,连总理衙门都派了代表来贺喜。
拜堂时,金道凤透过盖头下方的缝隙,看到程颐之锃亮的皮鞋和熨帖的西裤。这个细节让她想起寿宴上他穿西装的样子——与她想象中古板的旧式文人不同,她的丈夫似乎更接近那些开明的新派人物。
洞房花烛夜,当喜娘们终于退去,新房内只剩下新婚夫妇二人时,金道凤紧张得几乎窒息。程颐之轻轻掀开她的盖头,两人四目相对,都有些局促。
“累了吧?“程颐之先开口,声音比金道凤记忆中的要温和许多。
金道凤轻轻摇头,又点点头,自己也不知道想表达什么。程颐之笑了笑,起身倒了杯茶递给她:“喝点水,今天一天都没好好吃东西吧?“
这个体贴的举动让金道凤稍稍放松了些。她接过茶杯,小口啜饮,借机打量自己的新婚丈夫。程颐之约莫二十五六岁年纪,面容端正,眉宇间透着沉稳,眼神却比想象中柔和许多。
“我...我虽然知道这门婚事是父母之命,“程颐之突然说道,语气诚恳,“但我希望我们能成为相敬如宾的夫妻。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
金道凤没想到他会说这样的话,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在她接受的闺阁教育中,丈夫是天,妻子是地,何曾听说过丈夫询问妻子需要的?
“我...我会尽好妻子的本分。“她低声回答。
程颐之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点头:“时间不早了,休息吧。“
红烛高烧,罗帐低垂。金道凤僵硬地躺在婚床上,听着身边人均匀的呼吸声,思绪万千。这不是她少女时代幻想过的洞房花烛夜,但比起那些传闻中粗暴无文的纨绔子弟,程颐之至少给了她基本的尊重。
窗外,一弯新月悄悄爬上树梢,见证着这个不眠之夜。
---
三朝回门那天,金道凤早早起床梳妆。她特意选了一件淡粉色旗袍,既显气色又不失新妇的端庄。程颐之也很配合,准备了丰厚的回门礼。
“姐姐回来了!“刚进金府大门,金道凤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道友从影壁后冲出来,却在看到她身边的程颐之时猛地刹住脚步,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道友。“金道凤欣喜地唤道,想上前拉住弟弟的手,却被回门礼的仪式流程打断。
整个上午,金道凤都被家中女眷团团围住,询问婚后的生活。道友一直站在远处,眼神复杂地望着她。直到午宴后,金道凤才找到机会单独与弟弟说话。
“那天你为什么跑了?“她轻声责备道,“姐姐多希望你送我上轿。“
道友踢着脚下的石子:“我不想看着姐姐跳进火坑。“
“胡说什么!“金道凤皱眉,“程家待我很好,颐之也是个正人君子。“
“是吗?“道友冷笑一声,“那他前妻留下的三个孩子呢?姐姐知道吗?“
金道凤脸色骤变:“你...你怎么知道?“
“京城就这么大,有什么秘密?“道友眼中闪过一丝痛色,“程颐之前妻去年病逝,留下三个孩子。他守孝才半年就急着续弦,不就是找个保姆照顾他的孩子吗?“
金道凤胸口发闷。这件事,程家确实没提前告知,她也是婚后第二天才知道的。当时程夫人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西跨院住着颐之前妻留下的孩子“,便再没多说。程颐之本人也从未主动提及。
“这...这很正常。“金道凤强作镇定,“续弦本就为了照顾家室。我会善待那些孩子的。“
道友盯着姐姐看了许久,突然叹了口气:“姐姐变了。从前那个会和我一起偷看禁书的姐姐去哪了?现在你满口都是'本该如此'、'理应这样',活像个道学先生!“
金道凤被这话刺痛了:“道友,人总要长大的。你不能永远像个孩子一样任性。“
“我宁愿永远不长大,也不要变成你们这样虚伪的大人!“道友丢下这句话,转身跑开了。
金道凤站在原地,手中帕子绞得死紧。她没想到婚后第一次回娘家,就会和弟弟闹得这么不愉快。
“夫人,该回去了。“程颐之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金道凤慌忙擦去眼角的湿意,转身强撑出一个笑容:“好的,这就来。“
回程的马车上,金道凤一直沉默地望着窗外。程颐之看了她几次,终于开口:“和你弟弟吵架了?“
金道凤惊讶于他的敏锐,轻轻点头。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程颐之斟酌着词句,“我像他那么大时,也总觉得长辈们迂腐守旧。“
金道凤转头看他:“那你...现在怎么想?“
程颐之望向远方:“人越长大,越明白世事不是非黑即白。有些改变需要时间,有些传统也未必全无道理。“他停顿了一下,“不过这些话,你弟弟现在恐怕听不进去。“
金道凤若有所思。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丈夫的了解实在太少了。
---
回到程家后,金道凤做了一个决定——去看看西跨院的那三个孩子。
西跨院比想象中要偏僻许多,几乎位于程府最角落的位置。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年迈的嬷嬷在打盹。
金道凤轻轻推开正屋的门,一股药味扑面而来。屋内陈设简单得近乎简陋,三个孩子围坐在一张小桌前,最大的女孩正在教两个弟弟认字。
看到有人进来,三个孩子立刻站了起来,紧张地看着她。最大的女孩约莫七八岁,瘦得惊人,眼睛大得几乎占了半张脸;两个男孩一个五岁左右,一个看上去才三岁,都面色苍白,明显营养不良。
“你们...我是...“金道凤一时不知该如何介绍自己。
“您是新夫人。“大女孩低声说,拉着两个弟弟跪下,“给夫人请安。“
金道凤心头一酸,连忙扶起他们:“不必如此。我...我只是来看看你们。“她蹲下身,与孩子们平视,“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程婉如。“女孩回答,声音细如蚊蚋。
“婉如,好名字。“金道凤柔声道,“这是你弟弟们?“
婉如点点头,指了指大一点的男孩:“这是二弟程瑞。“又指了指最小的那个,“三弟程琮。“
最小的程琮突然咳嗽起来,小脸憋得通红。金道凤下意识将他抱起,轻拍他的背。孩子身上单薄的衣衫下,肋骨根根可数。
“怎么病得这么厉害?没请大夫吗?“金道凤焦急地问。
婉如摇摇头,眼中含泪:“嬷嬷说...说我们命贱,挺挺就过去了...“
金道凤胸口一阵刺痛。她紧紧抱住程琮,对婉如说:“去叫醒外面的嬷嬷,让她立刻去请大夫!就说是我说的!“
那晚,金道凤一直守在程琮床边,直到大夫确诊只是风寒,开了药,保证无性命之忧才离开。程颐之闻讯赶来时,看到的是自己的新婚妻子抱着前妻的孩子轻声哼唱摇篮曲的场景。
“道凤...“他站在门口,神情复杂。
金道凤抬头看他,眼中带着质问:“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照顾好他们?“
程颐之走进来,摸了摸程琮滚烫的额头,声音低沉:“我...我不知道他们过得这么差。母亲说孩子们需要静养,安排在西跨院,有专人照顾...“
“专人?“金道凤冷笑,“一个整天打瞌睡的老嬷嬷?“
程颐之面露愧色:“是我的疏忽。从明天起,我会重新安排。“
那夜之后,金道凤几乎每天都往西跨院跑。她给孩子们带去新衣服、玩具和点心,监督他们按时吃药、吃饭。婉如从一开始的警惕到渐渐接受这个温柔的继母,两个男孩更是很快黏上了她。
程夫人对此颇有微词,但碍于新妇刚进门,也不好明着反对。程颐之则默许了妻子的行为,甚至暗中支持。金道凤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找到了婚姻中第一个实实在在的支点。
---
时间如流水,转眼金道凤出嫁已近一年。这一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三岁的溥仪继位,朝局动荡不安。
1908年冬天的一个下午,金道凤正在教婉如绣花,突然收到娘家急信:金鸿煊突发中风,情况危急。
金道凤立刻赶回金府。父亲躺在床上,半边身子不能动,口眼歪斜,与记忆中威严的形象判若两人。金夫人哭成了泪人,家中乱作一团。
“大夫怎么说?“金道凤急切地问。
“说是脑溢血,就算保住性命,恐怕也...“管家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金道凤强忍泪水,开始安排各项事宜。这时她才注意到,家中少了个人:“道友呢?“
金夫人擦着眼泪:“那孽障...听说上海闹革命党,一个月前就偷跑去了上海,说什么要'追求新思想'...你父亲就是被他气病的!“
金道凤又惊又怒。上海确实风传有革命党活动,朝廷正在严查。道友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派人去找了吗?“
“派了,可上海那么大,哪里找得到?“金夫人哭道,“这孽障还留了封信,说什么'誓与腐朽的旧世界决裂'...他这是要毁了金家啊!“
金道凤安抚好母亲,立刻回家找程颐之商量。程颐之在总理衙门任职,消息灵通。
“确实不妙。“程颐之眉头紧锁,“近日朝廷正在严查革命党,上海租界里抓了不少人。若道友与他们有牵连...“
“能不能想办法把他带回来?“金道凤恳求道。
程颐之沉思片刻:“我试试看。但你要有心理准备,如果他真的参与了革命活动,恐怕...“
金道凤的心沉了下去。她突然意识到,曾经跟在她身后甜甜地叫“姐姐“的小男孩,已经长成了一个她完全陌生的青年。
三天后,金鸿煊的病情稍稳,金道凤却收到了另一个噩耗——道友在上海被捕,罪名是“勾结革命党,图谋不轨“。
这个消息彻底击垮了金鸿煊。老人在病榻上挣扎着写下几封求情信,要金道凤想办法救弟弟,随后再次中风,这次没能挺过来,撒手人寰。
金道凤在短短几天内经历了父亲病危、弟弟被捕、父亲去世三重打击,整个人几乎崩溃。是程颐之撑起了局面,他动用各种关系,花了大笔银子,终于在一个月后将道友保释出狱。
当金道凤在监狱门口见到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弟弟时,几乎认不出他来。道友瘦得脱了形,脸上带着瘀青,走路一瘸一拐,唯有那双眼睛依然倔强。
“姐姐。“他嘶哑地唤道,嘴角却扯出一个笑容,“我没错。“
金道凤再也忍不住,冲上去抱住弟弟,痛哭失声:“你这个傻子!差点害死自己知不知道!“
道友轻轻回抱她:“值得。姐姐,我见到了孙先生,听到了真正的救国之道。这个朝廷已经烂到根子里了,必须...“
“闭嘴!“金道凤厉声打断他,“父亲已经为你的事去世了,你还不知悔改?“
道友如遭雷击,整个人僵住了:“父亲...死了?“
金道凤泪流满面:“你满意了?为了你那套不知所谓的'新思想',气死了亲生父亲!“
道友踉跄后退几步,脸色惨白如纸。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转身,一瘸一拐地走向远处的马车,背影孤绝如荒野独狼。
那一刻,金道凤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她和弟弟之间彻底断裂了,就像摔碎的瓷器,再也无法复原。
---
道友回到BJ后,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不再高谈阔论革命理想,却也拒绝按传统为父亲守孝。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日整夜地读书写字,只有金道凤回娘家时才会勉强出来见一面。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土崩瓦解。北京城里人心惶惶,许多旗人官员纷纷变卖家产准备逃难。程家因为与北洋新派关系密切,倒不怎么恐慌,但金家这样的传统汉军旗人家族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天,金道凤回娘家与母亲和弟弟商议对策。
“我已经联系了天津租界的朋友,“程颐之对金夫人说,“如果局势恶化,可以先去那里暂避。“
金夫人六神无主,只是抹泪。道友突然开口:“不必逃。革命军不会滥杀无辜,只要剪了辫子,表明支持共和,安全无虞。“
“你说得轻巧!“金道凤忍不住反驳,“多少旗人家族被抄家灭门?怎能冒险?“
道友冷笑:“姐姐和姐夫这样的既得利益者,自然害怕变革。“
“你!“金道凤气得发抖,“这些年你读了那么多书,就学会了这样对家人说话?“
“家人?“道友眼神冰冷,“父亲去世那天,是谁指责我气死了他?这些年,是谁整天围着程家转,把程家的孩子当宝,却对自己的亲弟弟不闻不问?“
金道凤如遭雷击:“我...我那是...“
“道凤确实太关心程家那几个孩子了。“金夫人突然插话,“上次我给她那对翡翠玉镯,她转头就给了程婉如那丫头。那可是我们金家的传家宝啊!“
道友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受伤的神色:“原来如此。姐姐心里,早就没有金家了。“
“不是这样的!“金道凤急切地解释,“婉如那孩子体弱,玉镯能安神...“
“够了!“道友猛地站起来,“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金家的兴衰,不劳程夫人费心!“
“道友!“金道凤站起来想拉住弟弟,却被他狠狠甩开。
“对了,“道友在门口回头,眼神决绝,“我已经决定去日本留学。这个腐朽的国家,多待一天都让我窒息。“
金道凤呆立原地,看着弟弟离去的背影,泪水模糊了视线。她不明白,为什么姐弟之间会变成这样。她只是想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为什么在弟弟眼中,这都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窗外,秋风萧瑟,卷起满地枯叶。就像这个正在崩塌的帝国一样,金道凤感到自己生命中某些重要的东西,正在无可挽回地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