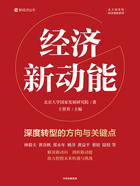
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内涵与实施路径[1]
黄奇帆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
新质生产力提出了一个逻辑内涵,主要讲这个时代以及当下为什么要把新质生产力的推进作为一个重大战略,直到“十五五”期间,乃至今后50年都要把这当作头等大事,其中有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当下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和必然选择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GDP的增长从1980年的大约2000亿美元到2020年的大约14.7万亿美元,总体上涨了70多倍。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持续高增长,是人类近几百年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此项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我们40多年里对资源、资金、劳动力的巨大且持续的投入。但是发展到现在,这种高速模式已经到了一种不可持续的状况。
资源投入方面,中国经济发展要源头减量,也就是资源消耗及单位消耗量要下降,能源节能减排消耗要下降。目标是力争到2035年,单位能耗、单位资源消耗下降到世界均值;力争到2050年,我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实现中国梦的时候,单位能耗、单位资源消耗达到发达国家的均值。
资金投入方面,从1948年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到2013年的65年间,中国的广义货币(M2)达到了110.65万亿元。2013年到2020年,M2在7年间新增了约100万亿元。到2023年年底,M2达到292.27万亿元,2024年1月末达到了297.63万亿元,中国货币发行的速度和规模实际也已经出现了一个不可持续的状态。什么意思?如果在20年前,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政府、银行在一年中进行调控,使M2增加1万亿元、2万亿元,股市会涨,房地产市场会涨,商品市场价格也会涨,GDP也会涨1~3个百分点。但是近年,M2即使一年增加20多万亿元,GDP增长也很慢,比如2023年M2就比2022年增加了20多万亿元,但股市没涨,房地产市场、商品市场价格都没有涨,钱在银行的账上悬着,银行的钱也到不了老百姓手中,到不了企业手中。看货币总量,觉得像通货膨胀;看市场,又觉得像通货紧缩。所以,再靠原来的模式不断投放货币来拉动经济增长已经不那么敏感,不可持续了。
劳动力人口投入方面,中国人口在1950年是大约6亿,1980年是大约10亿,到现在是大约14亿,处于一个不断增长的阶段,但是今后二三十年,人口会是一个下降的趋势。我们可以做一个静态的因子模型、理论模型或者一个概念模型的思考:按照现在的出生率,中国每年出生800多万人,现在的14亿人,在没有特殊干预的情况下自然增长,按人均寿命80岁计算,80年后就剩下7亿人,减掉了一半。因此在未来,中国像过去十年、二十年那样通过较高的劳动力投入带来人口红利,带来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以后劳动力每年会少几百万,十年就会少几千万,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推理,中国像过去那样靠资源投入、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拉动经济高速度、大规模增长的时代过去了。今后几十年,要靠新质生产力,靠技术创新,靠优势制度产生的资源优化配置,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比重。什么时候把这个短板补上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潜力就挖掘出来了,所以当下中央提出新质生产力正当其时。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路径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第一要义也是创新,本质还是创新。创新的形式各种各样,如我们说的三百六十行,每一行都有它相应的创新,那是不是三百六十行的创新统统都叫新质生产力?并不尽然。不要把新质生产力当作一个“筐”,什么事都往新质生产力里装。前段时间有记者报道某个乡政府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新质生产力,然后表态说要怎样把乡里的新质生产力抓好。这个表述的逻辑、语言、初心没什么大错,但是它的内涵是不对的,相当于把基层的所有活动都归到了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上,这就把新质生产力庸俗化了。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路径、实施措施是五大板块的五大颠覆性创新。所谓“五大板块”,就是指新能源、新材料、数字智能技术、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制造。这五大板块像五棵参天大树,每棵树各有若干枝干,枝干往上延伸还有细细的树枝和树叶,蔓延开以后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巨大的行业密集体系。“十四五”规划里提到的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都可以归在这五大板块里。因此,我们要围绕这五大板块形成的主导方向进行研发投入和颠覆性创新。
(1)颠覆性的理论创新。比如新能源理论创新、人工智能理论创新等,这五大板块,每个板块都可能出现从0到1的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和创新。
(2)技术上的颠覆性创新。有了理论创新并不等于有科研成果,理论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变成现实的产品或者成果,因此技术创新也十分重要。
(3)工艺创新。有了技术创新,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已经能够把理论模型变成实际成果,但是可能敲敲打打,做一个两个可以,要做几十万亿元的规模,就是大规模的生产,必须采用流水线,或者成熟的连锁工艺流水线,这也一定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有质量保障的流水线,而这种工艺流水线也需要创新。特斯拉的第一款车在2008年交付的时候,因为成本高,所以售价也很高,销量并不好。四五年下来,市场仍没有打开,市值也从1000多亿美元掉到了几百亿美元。之后,特斯拉来到中国,2018年签约,2019年初上海超级工厂奠基,在中国一年就能生产50万辆。这个规模达50万辆的生产线引发了马斯克的思考,他后来颠覆性地改变了工艺流程,把零部件组装式改成了压铸式,压铸一体化把许多零部件简化掉了,使得整体金属材料消耗减少了10%,线上组装成本降低了40%,这种改进可谓是一次工业革命。
(4)工具革新。人类历史上,很多工具的革新都能带来颠覆性的发展,比如说:有了显微镜,就能对细胞结构等进行分析;有了望远镜,可以对宇宙、航天领域进行分析;有了光刻机,可以做芯片。所以,工具上颠覆性的创新也是对时代的推进。
(5)要素创新。要素资源的颠覆性创新和现在的数据创新是一样的道理。
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态环境
任何一项技术创新都是不断分工细化的过程,分工细化以后就会有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会不断地产生非常具体的分工,就会不断地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
生产性服务业大体上有十个方面:一是产业链的研究开发;二是产业链的物流配送;三是产业链上的检验检测及市场准入;四是产业链上的金融清算与服务;五是产业链上的绿色低碳与生态环境保护;六是产业链数字技术赋能;七是产业链上的贸易批发采购,可以是线上的贸易批发零售,也可以是线下传统的贸易批发零售;八是产业链上各种专利商标或者品牌的宣传和保护;九是产业链上的各种服务外包,包括律师服务、会计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咨询服务、技术服务等等;十是产业链售后服务。
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这十种服务占GDP的比重越高,代表社会发展越先进,高质量发展的比重越高。未来,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会不断提高,十年二十年之后,当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60%~70%时,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总量里所占的比重也会达到60%以上。这是人类社会随着技术进步发展的逻辑性构架。在这样的构架下,服务业会出现五个特点。
一是越发达的国家,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越高。比如美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80%,其中三分之一是生活性服务业,三分之二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就是占GDP总量80%的服务业中有三分之二是生产性服务业,80%的三分之二就是53%,所以大致可以说美国GDP的50%是生产性服务业。而欧盟作为发达国家的组合体,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78%,78%里面有50%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就是GDP里面有大约40%是生产性服务业。2023年,我国GDP中服务业增加值占54.6%,其中50%是生活性服务业,50%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就是说GDP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在27%左右,和欧洲的40%、美国的50%比,差距较大。这也是短板之一,我们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二是服务贸易强。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服务贸易进口、出口会越来越多。中国2023年整个贸易当中,货物贸易占比超过80%,服务贸易占比只有12%,所以中国现在的贸易结构里,服务贸易比重不够。二十大报告提到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所以我们必须着力发展服务贸易,只有服务贸易强才能成为贸易强国。
三是当新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就会随之提高。这是因为生产性服务业里的各个要素都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增长有关。
四是当生产性服务业比重高了以后,价值含量、服务价值就会嵌入商品中。比如一款手机卖6000元,其硬件价值3000元,但是操作系统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也占到50%,价值3000元。所以越是高档产品,其内含的服务价值比重就会越高。
五是代表新质生产力的独角兽企业占比较高。当一个国家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比较高,达到30%、40%时,独角兽企业的占比就会比较高,随之全要素生产率比重、服务贸易比重也会比较高。
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的发展会带动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优化能刺激生产力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匹配的基础性社会制度,并进行制度化的创新。
第一,增加研发经费的投入。新质生产力要重视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研究制定“十五五”规划和2040年远景目标时应该提出一个逻辑:设定全国研发费用要占GDP的3%,那到2035年是不是应当进一步提升到4%?这个指标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化安排,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调整的。
第二,增加原始创新研发经费的投入。科研创新首先是原始创新、从0到1的源头发明创造、无中生有的创新。在这方面,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存在的问题是投资力度不够。到2035年应该力争使我国的原始研发创新投入占比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达到20%。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这个指标一调整,整个生产关系和新质生产力之间就比较匹配了。
第三,增强原始创新成果的转化力度。在研发成果的转化上,我国力度不够。也就是在从0到1发明以后,我国在从1到100的转化上力度不够。目前中国的转化量大体上是发明量的20%,在世界范围处于偏低的水平。任何国家的发明创造转化量都不可能达到100%,但应该达到40%、50%的水平。目前,我国的制度是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专利投资者占30%,发明者、发明团队占70%,看起来我国对发明团队高度重视,但实际上这些发明不见得能转化。最近这二十年,我国每年有上千个获得技术进步奖、创新成果奖的科研成果,但是很少有发明人因为知识产权变成亿万富翁,因为没有转化就没有产生生产力,就没有利润。而重视科研成果转化,还真要学发达经济体的做法。发达经济体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知识产权专利都被分为三个部分,也就是对于任何科学发明的知识产权专利,投资者拥有三分之一,发明者拥有三分之一,转化者也拥有三分之一。这样一来,发明者如果自己能把它转化成生产力,那就可以拿三分之二。发明者能发明,但不一定能转化;转化者情商高,懂市场,只要制度保障到位,就会有大量的转化者参与进来,推动创新成果的转化。美国的《拜杜法案》就是有关这方面的法律规范,推动硅谷成为全球研发创新及科研转化的高地。在这方面,我国还缺乏制度机制来保障转化者的利益。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这样的转化,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对于科研开发的投资、转化的法律制度,这也是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一环。
第四,建立健全培养独角兽的资本市场体系。好不容易有了从1到100的产品转化,怎样把这些产品大规模生产,形成独角兽企业,从而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这需要资本市场支持,需要私募基金、公募基金、天使基金的支持。虽然这些基金我们现在都有,也有二三十万亿元的资金量,但是大都以投资、投机为主,缺少耐心,很少有基金从产业萌芽状态就开始投入培养,都想吃现成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缺少耐心资本。所以,党的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发展耐心资本。
第五,解决数据产权问题。新质生产力是数字要素对传统要素的颠覆性创新。但数字要素的知识产权怎么清算?因为数字要素跟煤炭等消耗品不同,后者一用就消耗掉了,给你就是你的,而数据卖给你,你可以重复使用,可以不断使用,使用过程中数据有迭代,变成新数据,所以数据的产权、分配权、使用权,最初产生的效益和最终的效益怎么匹配,这方面的制度现在还没到位。在制度不到位的情况下,在不断推进数据活跃度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许多司法纠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要把这件事做好。
总之,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在五大板块的产业上发力,要在五个层次上进行颠覆性的创新,要培育和壮大生产性服务业,要着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要提供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制度保障。只有各方面综合发力,形成体系推进,新质生产力才能快速生成,并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从而为提升国家总体竞争实力、促进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提供坚强有力的生产力支撑。
[1] 本文根据作者2024年6月25日于“影响力·时代”峰会——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