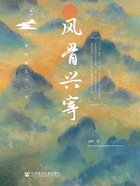
引言
中国古代散文具有非常悠久的发展历程,其产生可以上溯到上古时期的官府文书。唐宋散文则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长河中的一个新高峰,它继承了先秦两汉时期散文的创作传统,同时还吸收了六朝骈文中的一些艺术技巧,在这些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学特色和审美意蕴的优秀作品。其中所确立的书写范式和展现的艺术力量,又深深影响了明清散文的创作。即使是在现代白话文兴起一个世纪后的当下,唐宋散文的章法结构、语言艺术仍对今天的写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散文史的发展,按照前人的意见,大致可以分为先唐和唐以后两个阶段。先唐时期是古代散文产生和发展时期。文学史家认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尚书》,它是上古官府文书的总汇,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也已经具备了一些基本的文学特征。《尚书》中的文章结构趋于完整,有些篇章注重人物的口吻和语气,有些篇章注重语言的形象化,有些篇章则注重对场面的具体描写。后世的制诰、诏令、章奏,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由于《尚书》距离我们的时代太过于遥远,其中的一些记言文章佶屈艰深,晦涩难懂。所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1]从这种描述中可以窥见上古散文的最初面貌。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孕育出了各种新的思想,它们互相不断碰撞,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情状。散文在该时期也进入了全面兴盛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前者以《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国语》等为代表,后者以《老子》《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为代表。这些散文言语犀利、情采并茂,力求在表达上具有最大的说服力和鼓动性,从而展现出一种崭新的文风。不仅如此,这些散文还非常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富有启发意义。其中的许多小故事写得饶有风趣,常隐含着耐人寻味的意旨,成为流传后世的成语典故。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狡兔三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亡羊补牢”等成语,沿用至今,极具生命力。大家在学生时期或许已经接触过一部分这类文章,譬如《烛之武退秦师》《城濮之战》《孟子见梁惠王》《逍遥游》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篇。
两汉散文艺术又在前代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司马迁以生命的体验来实现立言的崇高目标。他饱含着深厚的情感运笔行文,使《史记》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表现出磅礴的气概和雄浑刚健的艺术力量,对后世传记文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汉初贾谊、晁错、枚乘、邹阳等人创作的政论文风格朴实,议论酣畅,意气纵横,尽所欲言,具有将说理与情感、气势、形象相结合而动人心魄的特色。《淮南子》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基础上,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它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许多神话材料,呈现出宏大雄奇的特色。东汉时期,班固的《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以实录精神叙写社会各阶层人物,平实中见生动,与《史记》一道,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整体来看,汉代散文风格朴实,造诣突出,得到了后世的有力肯定,唐宋以来的诸多习文者也往往以三代两汉文章作为学习的典范。
魏晋时期,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促成了思想新变,散文也从史学、经学中独立出来,政教色彩减弱,表现出通脱自由、持论清峻的文艺特征。建安、黄初时期的散文,曹魏成就最高,吴、蜀次之。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指出,曹魏散文与汉代散文不同之处在于:“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一也;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奏疏之文,质直而摒华,二也。”[2]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质朴简明,曹丕《与吴质书》情真意切,诸葛亮《出师表》文辞笃实,忠悃之情跃然纸上。魏晋之际,受到玄学清谈风气的影响,散文或为玄理之辩,或多愤世之词。嵇康思想新颖深刻,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3]其代表作《与山巨源绝交书》立意超俗,行文精练。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洒脱奔放,语重意奇,发前人之所未发。
西晋散文注重形式技巧,情文兼善。李密《陈情表》剖陈深衷,言辞恳切,笔调哀婉,君主为之动容。潘岳、陆机则以辞采华丽著称,前者为文言情至深,善为哀辞;后者天才秀逸,下笔藻翰精美。东晋散文受到玄学和儒学的双重影响,审美风格趋于平淡。王羲之《兰亭集序》,情理融会自然,清隽潇洒;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高标卓立,《桃花源记》朴淡浅净。这一时期文体骈俪化的风气逐渐盛行了起来,出现了全篇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的骈文。这种创作风气在南朝时期进一步发展,文章骈俪的形式更加精巧,华靡的时代风尚也于此推波助澜,使得无韵的散文被归入“笔”,即应用文的范畴,文体功能被逐渐削弱,创作呈现衰颓之势。这一时期,除了部分历史地理类的著作,如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外,散文基本上被骈文取代。
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原本属于散文写作的范畴内,骈文也经常“闪亮登场”,大大挤占了散文的空间。在范晔《后汉书》中,骈文时时见诸字里行间,其论马援曰:“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己,以之断义必厉。”[4]骈体行文,堆叠拖沓,和《史记》《汉书》的行文利落相比,让人感到阅读起来不够流畅洒脱。文章骈俪化大行其道的趋势在当时也受到了一些反对。西魏宇文泰把苏绰模仿《尚书》所作的《大诰》定为各种体裁文章的“准式”。隋文帝杨坚下诏命令“公私之翰,并宜实录”,并治罪以华艳词句写文表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治书侍御史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称: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之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5]
但文风的流行似乎是有“惯性”的,它并不一定随着某个王朝的结束就戛然而止。隋文帝的行政命令没能有效解决文风问题。散文的真正复兴,要等到中唐韩愈、柳宗元登上文学发展的历史舞台以后。在此之前,从初唐到中唐,许多文人为文风的改变做出了探索和尝试。梁肃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称:“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李华)、萧功曹(萧颖士)、贾常侍、独孤常州(独孤及)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6]也就是说,在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之前,唐代的散文至少已经出现了三次变化。按照葛晓音先生的观点,初盛唐散文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唐太宗贞观元年到唐高宗时期,代表作品有魏徵的《论政事疏》《十渐疏》《论治道疏》、王绩的《五斗先生传》《醉乡记》《答冯子华处士书》等散文。第二阶段是武则天至唐中宗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武后爱好文章辞采,讲求对偶、雕琢辞藻的骈文几乎占领了文章创作的所有领域。在这一时期的文士中,笔者认为陈子昂(661~702)很值得注意,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提倡恢复古道,反对雕饰,强调比兴寄托,实际上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扫清了障碍。第三阶段是盛唐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到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之前。这时期代表作品更为丰富,如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张九龄《敕安西节度使王斛斯书》、李白《与韩荆州书》、王昌龄《上李侍郎文》、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招素上人弹琴简》、李华《吊古战场文》、元结《右溪记》等散文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7]这个划分方法条理清晰,能使我们迅速概览初盛唐散文的基本面貌。
在本书中,初盛唐散文部分主要由前三讲组成。分别是“魏徵与王绩:初唐时期的仕与隐”、“陈子昂:风骨与兴寄的呼唤”和“李白与王维:盛唐的信笺”,均以作家为线索,向外关联其时代风尚,向内探讨其创作特征。此后的第四讲“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第五讲“柳宗元:‘独钓寒江雪’”,则围绕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创作展开。韩愈一生宗经明道,堪称一代宗师。他的议论气势充沛、先声夺人,《论佛骨表》义正辞直,充满情感张力,后世称其“允为有唐一代儒宗”。[8]他笔下的人物则活灵活现、各异其面,如张巡之严肃刚毅,南霁云之豪气干云,贺兰进明之阴险狡狯,无不声口毕肖,读之使人犹如身临其境。柳宗元的创作则“牢笼百态”,摹景、写人、状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他的“永州八记”将自然山水与主体人格相联系,借山水之形胜抒胸臆之郁结,对后世山水游记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寓言散文则因物设譬、意味深长,《三戒》《 蝂传》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
蝂传》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
自韩柳以后,散文创作者虽然不少,但他们的成就并未超过韩柳。至晚唐,骈文又重新占据了文坛主流地位。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韩门弟子的散文虽然语言畅达、条理清晰,但对于散文的文学性不太关注。他们的散文叙述详尽却缺乏感染力,因此难以动人心魄。其次,一些作者在文章中喜欢使用冷僻、怪异的字词,其本意是借此产生一种令人过目难忘的陌生感和新鲜感,实际上却使文章晦涩难懂。生造出的词句使人不知所云,因此流传不广。最后,散文本身具有应用性特征,在实际书写中又与具体事件、名物、人际交往相关联,创作者如果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敷衍为文,就很难把散文的精神气格表现出来。这种情况也向我们揭示出,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它的成就并非一蹴而就,需要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其中,做出不懈的努力。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散文作家作品值得我们关注。为拾“遗珠”,本书第六讲“吉光片羽:唐代散文遗珠”选择了天宝时期李华的《吊古战场文》、中唐白居易的《庐山草堂记》、晚唐皮日休的《读司马法》进行赏析。由此,唐代散文中的名作庶几一览无遗。
宋初文风沿袭晚唐五代,纤秾有余而未见自家面目。其后,又有“西昆体”“太学体”等风格陆续主导文坛,前者伤于“缀风月,弄花草”,[9]后者又流于艰涩险怪、脱离实际。这一阶段可谓北宋初期文学发展的“曲折探索”时期。本书第七讲“风雅再临:北宋初期的散文”对宋初散文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与介绍,并围绕王禹偁《黄冈竹楼记》、范仲淹《岳阳楼记》两篇名作分别设置章节进行精讲。经过柳开、王禹偁、范仲淹等人的不懈努力,至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文风变革由此打开了新局面。此后,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新人登上了文坛,他们纷纷写出时代的悲欢与心中的歌哭,为北宋散文创作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书第八讲“欧阳修:‘醉翁’的胸襟”围绕欧阳修的生平经历与文学贡献展开。他的名作《醉翁亭记》和《祭石曼卿文》脍炙人口,在这一讲中我们也会逐一赏析。曾巩和王安石既是挚友,又是当世一流的文学家,第九讲“曾巩与王安石:平和简练不寻常”就以他们二人为中心进行相关作品分析。曾巩《醒心亭记》和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又都与欧阳修有直接关系,故而第八讲、第九讲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单元组合。第十讲“苏洵与苏辙:劲健沉稳有余响”、第十一讲“苏轼:‘坡仙’的文法”则以“三苏”的创作为中心,也可以视为一个单元组合。苏洵的《六国论》纵横恣肆、气势恢宏,苏辙的《武昌九曲亭记》叙述细腻、灵动如画,而苏轼更以其不世出的天才之力,为中国古代散文艺术长廊贡献了诸多名篇,《留侯论》《日喻》说理生动,前后《赤壁赋》珠联璧合,均堪称传世名篇,使人感到回味无穷。
除了以上名家外,宋代还有两位作家值得我们关注。其中一位是女作家李清照,她在《金石录后序》中叙述生平坎坷,行文绵密,极富真情实感。另一位是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在《指南录后序》中写尽一腔悲愤,其中所流露出的拳拳爱国之情,千载之后仍动人心魄。由此形成第十二讲“李清照与文天祥:忧国伤时正气彰”的主要内容。
以上就是本书所精选精讲的20位唐宋散文名家名作。从魏徵、王绩、陈子昂、李白、王维、李华,到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皮日休;从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到李清照、文天祥。他们的作品独出机杼,脍炙人口,或引经据典发人深省,或慷慨激昂饱含衷情,从中可窥见唐宋散文的创作理路、作家本人的人生际遇和唐宋社会转型期的宏大时代变迁。
唐宋散文对后世散文创作的影响极为深远,历代传诵不衰。明清散文的发展受到了唐宋散文的直接影响,刘基在《卖柑者言》中借小贩之口,对世道人心进行了犀利的讽刺,其中隐约可见柳宗元的寓言笔法。宋濂《秦士录》中的人物细节饱满,神采飞扬,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可谓一脉相承。《桃花涧修禊诗序》《环翠亭记》,下笔清秀简洁,又好似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至明代中期,“唐宋派”崛起于文坛,大力提倡学习唐宋散文。茅坤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选辑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家文章共164卷。其中对每家又各附有解析性的说明。这个选本在当时和后世有很大影响,成为千万读书人初学文章的门径,几百年来盛行不衰。“唐宋八大家”的说法也由此流行开来。清代古文名家辈出,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引领了一代风气。以姚鼐、刘大櫆、方苞为代表,他们写文章师法欧阳修和曾巩,要求立论鲜明,语言简洁顺畅。桐城派弟子甚多,其文学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写作逐渐流行起来,但唐宋散文作为中国传统文学创作典范,仍然对我们今天的语言表达与文章书写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1]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进学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54页。
[2]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第35页。
[3] 嵇康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卷六《释私论一首》,中华书局,2016,第402页。
[4]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第852页。
[5] 《文苑英华》卷六七九《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华书局,1966,第3502页。
[6] 《全唐文》卷五一八《补阙李君前集序》,中华书局,1983,第5261页。
[7] 葛晓音:《唐宋散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3~6页。
[8] 康熙御选,徐乾学等辑注《御选古文渊鉴》卷三五《论佛骨表》,文渊阁四库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1页。
[9]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陈植锷点校,中华书局,1984,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