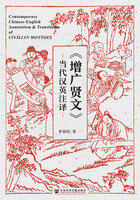
第1章 前言
作为蒙学读物之一,《增广贤文》流传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自诞生之日起,《增广贤文》一直滋养着中华文化而为民众喜闻乐见。书中的内容涵盖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民众生活诸多感悟与生活哲理的凝练,是华夏文明哲思的提炼与结晶,是中华诸多教育理念、行为准则、处世之道、人生真谛等的集大成者,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十分突出的启蒙功效,实为优秀中华典籍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增广贤文》通过汇编前人的论述,既宣扬了真、善、美的人生态度、处世之道,兼具教化与点拨之功,又阐发了人性弱点、人间世事的错综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等,可视为醒世良方。通俗易懂是《增广贤文》的显著特色。只要对其认真探究,就不难发现书中绝大部分句子形式对称、文字隽永、韵味十足、朗朗上口、自然流畅、寓意深邃,高超的语言艺术尽在其中。书中阐发的多数观点与认知对人们世界观的形成具有启迪作用。书中也不乏鼓励人们以处事不惊、深谋远虑、与人为善、灵活多变、细致入微的方式洞察世事,不把问题做简单化处理、追求超凡脱俗境界等理念,给人带来无限的裨益,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也有少数观点存在偏颇,显得冷酷无情;有些论述前后矛盾,甚或让人产生错觉,需要对它们认真加以甄别。总体而言,书中内容的积极意义远胜于消极意义。《增广贤文》的大多文句源自四书五经、古典诗词、史学名著、佛道经书与民间广为流传的谚语和格言等。相较于《三字经》《弟子规》等蒙学读物,它填补了蒙学领域重知识说教、重行为指导而缺乏说理论证的空白。无论文字形式,还是思想内容,《增广贤文》充满中华文化简约与深邃的特性,启蒙与教化作用突出,具有很高的实用与研究价值。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重经济轻文化思潮盛行,中华传统文化遭到冷遇,《增广贤文》也莫能例外,这令人倍感失落。就年轻一代而言,说到《增广贤文》已然十分陌生。要让当下青年人在短时间内熟知、理解与掌握如此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品非一日之功。为扭转当下局面,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让年轻一代受到中华传统文化更多的熏陶,激发起他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之情,重新对该书做出适切的注译是必要的。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优秀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常言道,要让他人了解你,你一定得先了解你自己。对《增广贤文》进行注译兼具让他人了解和了解自身的功效。为以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打开汉语语言知识的一扇窗户,让海外人士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典籍进行注译是必不可少的。
在国内,对传统典籍作品进行注译的作品已不在少数,但是结合英语进行注译的作品可谓凤毛麟角。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国学经典,助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走的路还很长。用英语注译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经典《增广贤文》,势必助推中华优秀文化向海外传播。
本书以上海昌文书局印行的《绘图增广贤文》(1946年版)一书为底本进行注译,保留了该版本的绝大部分内容,而对其中一些境界不高、负面消极乃至与当下格格不入的内容做了删减,同时,也从其他版本中吸收了少量思想健康、适应时代之需的内容。对照了近年推出的多个汉语注译版本,注译者发现该书局印行的《绘图增广贤文》以传统的版式加以刊印,除与现代书籍的刊印方式有所不同外,呈献了早期作品的阶段性特征,凝聚的是古代士大夫和平民百姓的情怀与心声,其内容可谓当初思想的物化,它们既来自民间,也适于在民间传播。该版本不失原汁原味,从头至尾未见任何注释,绘图也相对简单,这使对该作品的诠释与注译有了更大的空间。考虑到这些因素,注译者依据上下文语境,利用相关工具书,以现当代汉语为基础,对该书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诠释、分析、评价与注译。从生僻的词语到较为生疏的句式,再到复杂疑难的句意,注译做到尽可能详尽。《增广贤文》中所反映的语言风格比较传统,注译者着力改变其固有的表达方式,代之以通俗易懂的现代汉语行文。对其字里行间的深意,多采用释解(interpreting)的方式。释解力图既不忽视明清时期的表达风格,又以现代汉语的行文方式对原本的思想内容进行再现,尽可能做到既不偏离固有意义,又符合时代要求。
《增广贤文》的句子基本都以对偶、对仗形式呈现出来,音韵规整、格律有致、抑扬顿挫、言简意赅、流畅易懂、特色鲜明,每组句子聚焦于一二个话题,语义清晰、功能明确。对《增广贤文》所进行的注译包括言内注译和语际注译两种。语际注译重点关注了两种语言在音、形、义方面的巨大差异。为了使这种差异得以弥合,避免形式上的不可调和性,注译者把关注点置于语言的信息与功能上,多采用变通手段,尽可能使书中内容既显得简单明了,又不至于背离原文的寓意和旨趣;既保持原文意义的完整性,又尽量将译语的行文风格呈现出来。为了使诸如音、形、义等要素在汉英两种语言之间较好地实现对接或转换,注译过程大致如下:以原文的话题为基础,分立出话段,以每个话段为一个单元,首先就单元中的重点字、难懂词、特殊句式进行考察,然后挑选出重要部分,析出关键词语或句式,再配以简易的英文注释,从而保证对原文的注释与翻译进行主次分明的转换,最大限度地实现两种语言在信息和功能上的呼应;原语的句式和句意不能在译语中完全对接的,根据词性或句式的要求做必要的调整,以意译为主,直译为辅。其间的句式、话题析解与翻译建议部分对本话段的句式进行说明,对隐含的实际意义进行解读,并尝试提出翻译建议,最后把汉语话段翻译成现代英语话段。
《增广贤文》集中体现了汉语优美的特点,在传神达意的基础上,突出格律与韵律的工整性,令人赏心悦目。《增广贤文》的文句源自众多经典文本,因此,风格多变自不待言,而且每个话段的思想、主题完全不同,其字里行间蕴含的意义又十分丰富,这些也给注译或翻译造成了困难。为了处理好每个环节,本注译包括五个部分:①原始话段,根据思想性、语义的相关性与完整性析出;②词、句注译,对每个话段中的重点词语、句式进行考察后加以选择,然后给出语内、语际的相关注译;③现代汉语译文,把原始话段翻译成现代汉语;④句式、话题析解与翻译建议,主要针对该话段的句式做出明确的说明,分析其意义或寓意所在,提出汉译英的建议;⑤汉英翻译(Chinese-English version),将此话段的汉语翻译成英语。
将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为满足当代读者的需要去重新组建话段,确实是难点之一。一方面根据注译者的理解,做出必要的引申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采用汉语权威工具书中的解释,避免误导读者更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这种情况属于比较表层的工作。循着注解、分析、诠释与翻译的思路,读者对每个话段的理解就能够比较透彻,领悟其意义也能够比较到位。从上述五个方面着手对《增广贤文》的内容进行注译,是以帮助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全方位地理解与掌握中华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以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为目的的;为提高世人解读与领悟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兴趣,使中华文化在海外得以顺利传播做好铺垫。
将现代汉语翻译成英语,如何遵照英语的建构方式去重组话段,在英语信息结构得以合理建构的前提下,保证汉语的话题信息遵循译语的认知规范,即恰如其分地实现从语义结构到认知模式的建构是汉英翻译过程中译者所遭遇的难题。在语言运用中,无论是语内翻译,还是语际转换,认知问题并不容易做出解释。操不同语言的人在使用语言时反映出对主客观世界的不同看法,即看问题所采取的取向存在差别,而这种差异往往通过语言反映出来。世界上有许多客观存在,但在不同民族的人看来,其出发点、存在方式与表达手段等各不相同,在汉英两种语言之间要实现转换,的确困难重重。如汉语中突出人称,英语中喜用物称;汉语句子中没有主语属正常现象,而英语中主语基本不可或缺;汉语中少用或不用被动语态,英语中被动语态的使用却司空见惯。不符合译语读者的认知表述终究难以为译语读者接受,造成沟通失败就在所难免,本书注译过程中遇到的此类难题难以胜数。为满足译语读者的认知需要,尽量使语言所反映的认知问题在注译中实现有效转换,是此次注译中最为需要排解的问题之一。所幸的是,经过努力这类问题已较为妥善地得到解决。当然,其中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如前所述,汉英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差异,从词句形式到构成话题的上下文语境,再到篇章功能之间都存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使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能够顺应彼此的认知取向实在是一桩难事。在汉语中,句子无主语是常见的现象,例如,“三思而行,再思可矣”“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都看不出主语,但显然是对人的行为的描述,其中的主语隐含是十分清楚的,但对于英语读者而言却是令人费解的。要将汉语句子转换成具有形式化特征的英语,我们必须就其形式化的重要特征加以考虑。英语所谓的形式化特征完全可以用“主语+Verb”的结构作为代表。另外,英语句子中的词性分工尤其明确,词性的不同决定了其在句子中的成分及角色不同,如只有名词、名词性结构、非谓语动词或名词性从句才能担当主语、表语或宾语,其余成分则无法担当句子中这些角色,也只有这样,其篇章组织才有条不紊、俨然有序。如不然,形式即意义就无从成立,此次注译在这方面做了重点考察。而在汉语中,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偏正结构、联合结构、动补结构、主补结构等在主位位置或担当主语的角色却是十分常见。汉英两种语言在行文过程中表现了不同方式,前者更多地注重自身的功能和意义,即如何做到“传神”;后者在建构句子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如何显形,很多情况下,“形式决定意义”这一语言事实完全可以得到验证。将汉语翻译成英语,先洞察两种语言的差异,而后着重于汉英词汇的意义及其语法功能的呼应,最后考虑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应对从形式到意义的相互衔接。
据上所言,严谨、细致地力求实现两种语言功能最大化自然就成了此次注译的重中之重。汉语《增广贤文》绝大部分句子以对偶句的形式出现,整齐划一、音韵铿锵,将其翻译成英语,要完美地在形式和音韵上对接并不容易。针对这一点,变通便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在将《增广贤文》翻译成英语时,为实现目标语的形式而牺牲原文结构是此次注译中常有的现象。有鉴于此,在对《增广贤文》进行注译的过程中,描述性方法得到落实,规定性原则已不再适用此次注译。通过释解(interpreting)手段的运用,对原文中所隐含的意义进行深入的挖掘,两种语言的形式和内容难以贯通的问题随之迎刃而解。此外,对消除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隔阂,本次注译也做了较为仔细与周详的工作。
本书的注译,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所难免,恳请阅读此书的海内外读者、中华典籍翻译爱好者批评指正。
李英垣
201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