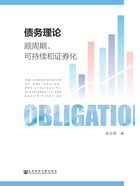
第三节 研究创新
一 研究的创新点
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书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创造性地提出“债务的三大特性”这一说法,将债务的顺周期性、可持续性与证券化这三大主要特性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以此来展开对债务理论的研究。结合中国现实与国际经验之后,可以发现,关于“债务的三大特性”的研究不仅仅是对过去和现在的总结与反思,更是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重点,本书可以算是一种“抛砖引玉”式的探索。
二是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融入历史和法律等其他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以此来从根本上探寻“债”与“债务”等概念的本质和源泉。经济学的历史才不过二三百年,但本书的研究对象“债”与“债务”早在公元前便已存在,因此,借鉴历史和法律等方面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综合运用这些研究成果更能深刻地揭示出债务及其三大特性的真实作用与实际价值,以此来避免“管中窥豹、井底之蛙”的局限。
三是对比之前的研究,有关债务的三大特性——顺周期性、可持续性与证券化的研究均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和改进。具体而言,对于债务的顺周期性,基于“金融不稳定”理论和“金融加速器”理论,本书不仅构建起一个融入债务动态变化的宏观动态模型,而且更为深入地阐释了金融体系从稳定状态到不稳定状态演变的深层原因;同时,本书还从货币政策调控的新视角出发,在一个自然实验的框架内,采用倍差法的检验策略,证实了融资结构这一微观基础的存在性,也为理论提供了相应的微观证据。对于债务的可持续性,结合中国实际,本书区分中央和地方来分别探讨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以避免片面地解读中国特殊的政府债务问题;在此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曾经历过的发展历程,从中提炼出经验和教训来指导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避免落入“债务陷阱”。对于债务的证券化,2008年金融危机引起了学术界对以影子银行体系为代表的债务证券化的反思,但当前多数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停留在对相关概念、定义和分类的简单梳理上,而本书从影子银行体系的宏观效应入手,针对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是否抑制了传统的利率传导机制进行经验研究,并探究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
二 不足之处
正是因为首次提出“债务的三大特性”这一新说法,所以,本书的实际研究必然会存在一些局限与不足,值得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本书的不足之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的具体载体。尽管本书是将债务的顺周期性、可持续性与证券化这三大主要特性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但在实际的分析和论证过程中,又分别以银行信贷、政府债务与影子银行体系作为“债务的三大特性”的具体载体进行相应的分析阐述。就某种程度而言,这就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债务的证券化部分,证券化不过是影子银行体系的一部分,但受到中外金融环境差异以及数据可得性的局限,为此,将有待未来的发展而进一步完善。
二是研究数据的局限性。对于债务的研究,最困难的便是缺少相应的债务数据。莱因哈特和罗格夫(2012)指出,在大多数国家,与其自身的历史周期相比,债务(特别是国内债务)的历史数据都很难获得,即使有这样的债务数据,其透明度和质量也均不理想。对于中国的数据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数据的透明度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不过,相关数据的周期仍较短,再加上统计口径也在不断调整,显然降低了数据之间的可比性以及不足以支持很多宏观时间序列方面的研究。此外,地方政府层面的数据质量明显差于中央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数据更是难以获取。因此,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和质量的提升,未来的研究将更能探讨债务问题背后的数量性关系。
[1] 这里的发达经济体共包括22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及欧元区的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日本、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美国;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有21个国家和地区,分别为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中国香港、匈牙利、印度、印尼、以色列、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波兰、俄罗斯、沙特、新加坡、南非、泰国、土耳其。以上数据来自国际清算银行。类似的国际比较,可参见Buttiglione et al.(2014)。
[2] 有时,也常把“负债率”称作“杠杆率”。
[3] 引自鲁迅的《二心集》之《习惯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