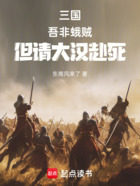
第54章 寻才论道
暮夜之际,一封急信自南皮而出,快马疾驰奔赴修县。
至次日午间,信使方抵城下。
修县地处渤海郡边陲,接壤四郡,与青州尤为邻近,向来是兵家纷争、兵乱频仍之地。
但此番信使一路畅行无阻,并未遭遇青州黄巾来犯。
信使翻身下马,向着城头守卒高声喊道:
“南皮来书,求见将军!”
城头上,黄巾军张字大旗猎猎作响。
旗下一人头戴铁盔,探出脑袋,扶盔俯视:
“兄弟稍候,城门即刻便开!”
话音刚落,厚重的城门缓缓开启,发出嘎吱声响,恰似老旧车轮转动。
信使向城上抱拳行礼,牵着马匹大步入城。
经过城门时,见一群匠人正抬着门。
好奇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之前青州人蜂拥而至,连城门都挤坏了,不得不重新修缮城门。
“难怪白日无风无波,城门却紧闭着,原来是这么回事,只是青州人真有这么多嘛?”
信使暗自嘀咕,旋即继续前行。
修县街道相较南皮狭小许多,道路状况亦差。
然而,街市之上氛围安逸祥和,两侧小贩鳞次栉比,全然不见战乱频繁的景象。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街道过于拥挤。
信使之前还不信,现在穿过城门,亲眼见到,也是不由吞咽口水。
无奈之下,他只好硬着头皮,牵着马,在长街中艰难前行,这时候他感觉自己都要被人群挤扁。
好不容易行至县衙门口,衙前辅兵告知将军并不在此,让他原路返回,前往城南军营找寻。
信使无奈,只得再次在拥挤的街道中穿梭,前往城南。
抵达军营前,信使急忙询问:
“将军可在营中?”
守卒伍长见其一来便打听将军下落,立刻上前搜身,边搜边问:
“天王盖地虎,你是哪部人马?”
信使挠头答道:
“宝塔镇河妖,我乃南皮辅兵。”
守卒伍长搜无所获,翻了个白眼,拍了拍信使:
“是辅兵就直说,什么南皮驿卒?咱们军中何时有驿卒了?”
信使憨笑着点头,说道:
“驿卒之名听起来好听些。我来之时听闻浮阳、章武已被收复,渤海全境皆归我军,日后难道不设驿站吗?”
守卒们听闻,先是面露喜色,随即哄然大笑:
“好啊!渤海终于平定,要不了多久,咱们就能卸甲归田了。”
众人一边笑着,一边打开营门。
此时,一名守卒对信使说:
“小子,与其想着当驿卒,不如随我们回乡种田。要是将军不打算设立驿站,你岂不是白费心思?”
信使摇头笑道:
“这绝无可能。有了驿站,军情政令方能迅速传递。将军深谋远虑,必定会设立驿站,到时我定要当个专职驿卒。”
守卒伍长笑着接话:
“好了,这些都是以后的事,现在跟我去见将军。”
信使点头,紧跟伍长身后。
来到主将帐外,几名亲卫挺立门前,纹丝不动。
守卒伍长上前抱拳行礼:
“将军,南皮信使求见。”
彼时,张旸正在帐中休憩,被喊声惊醒,伸了个懒腰,回应道:
“让他进来。”
亲卫立刻引领信使进入营帐。
信使一见到张旸,急忙抱拳行礼:
“将军,南皮突发变故,焦触渠帅命我送来书信。”
言罢,将手中书信递给亲卫。
亲卫转呈书信,张旸迅速展开。
刚看第一行,眉头便紧紧皱起。
看完书信,张旸长叹一口气,问信使:
“南皮如今还纷争不断吗?”
信使摇头苦笑:
“南皮如今人口锐减,五不存一,南城几乎荒无人烟,众人皆沉浸在悲痛之中,并无冲突发生。”
张旸微微颔首,放下书信,对信使道:
“你明日一早再返程,届时我修书一封,你带交焦触。”
“喏!”
信使抱拳领命,退了出去。
张旸坐回原位,紧攥书信,头疼地轻拍额头。
他原以为王六会心软,或许会让己方将士过度劳顿,没想到王六竟使出这等心计,致使南皮人口锐减,远不及修县,实在是得不偿失。
若按他原本谋划,集中兵力镇压反叛,断不会牵连如此众多百姓。
“唉,说到底,还是身边缺乏足智多谋之士。否则,这等计策运用得当,不失为一步妙棋。”
张旸摩挲着下巴,思索着焦触信中所述王六的所作所为。
他不得不承认,王六跟随自己以来,长进不少,只是实用和理论完全是两码事。
离间计本为诡道,更适合坐山观虎斗。
可如今南皮城中黄巾军才是强势一方,其余人如同待宰羔羊,使用此计稍有差池,便会惊乱局势,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好在焦触处理果断,否则己方将士必定损失惨重。
不过,经此一役,倒也解决了张旸的心头大患。
沉思片刻,张旸拿起矮桌上的毛笔,在黄纸上挥毫书写。
写完后,轻轻吹干墨迹。
信中,他并未责备焦触,毕竟这类事情更适合当面沟通。
他在信中给予焦触安慰,分析了渤海及南皮当前局势,并提出诸多提醒。
写完信,张旸用砚台将书信压住,起身走出营帐,准备前往校场巡逻。
然而,还未走到校场,营外便匆匆跑来一人,正是修县县令封当。
封氏与冀氏乃是修县当地名门大姓,封当身为封氏家主,为人极为圆滑。
张旸率军抵达修县时,他非但没有逃走,反而捧着官印出城迎接,还自掏腰包置办接风宴,将大军上下安排得十分周到。
尤其是在接风宴上,张旸提出各家大族按每人六亩地留存田产,其余田产上交的要求时,封当率先响应。
张旸对此颇为满意,因此封当依旧担任修县县令。
平日里,封当除了处理政务,很少来军营,此番前来,定有要事。
张旸满怀好奇,快步迎上前去,笑着问道:
“伯轩兄,今日前来,所为何事?”
封当气喘吁吁,连声道:
“将军,可还记得我曾与您提及的元皓先生?”
张旸一时没想起此人是谁,不禁愣了一下。
封当见状,连忙提醒:
“就是田家之主。”
张旸一听“田”字,恍然大悟,欣喜问道:
“他有消息了?”
封当点头笑道:
“正是!田家传来消息,元皓先生不日便将返乡。”
张旸闻言,拍手称好:
“好!实在太好了!伯轩兄此讯来得太及时,届时我定要亲自登门拜访,以示诚意。”
-----------------
眼睛一睁一闭,一天就这么过去。
天光甫现,张旸身披犀甲,腰悬环首刀,于亲卫簇拥之下,巡视营伍。
此时,万余黄巾将士正自行操练,见张旸身影,瞬间整肃阵列,甲胄铿锵,声震营垒。
张旸引步疾驰,绕营三匝,数万将士紧随其后,如长龙蜿蜒而出。
队伍踏街前行,脚步声如雷贯耳。
街边百姓纷纷驻足,夹道而观。
黄巾入驻修县时日虽短,然开仓放粮,平冤狱、除恶霸,青州之地渐趋安宁,百姓感其德,见张旸率军跑过,皆鼓掌欢呼。
张旸边跑边向百姓拱手示意,回应众人盛情。
待跑完三圈,百姓呼声愈烈,纷纷高呼“再来一圈”。
然而练兵诸事繁多,张旸只好笑而不语,挥了挥手,便遂率众回营。
众人稍作休憩,便开始用饭。
饭毕,信使匆匆来见。
张旸将书信递予信使,问道:
“汝观修县与南皮,何处为佳?”
信使双手接过信笺,挠首思忖后,直言道:
“某虽仅至修县一日,却觉此地远胜南皮。此间百姓安乐,对我等极为拥护。”
张旸闻言,抚掌大笑:
“如此看来,我等所行之路无误。南皮之弊,在于当地小民昏聩,大民贪婪。回去转告焦触,一切依计行事,不可有误。”
信使拱手顿首,应道:
“喏!”
言罢,信使转身欲离,准备连夜赶回南皮。
刚至营门,守卒拦住其去路,指向一旁等候的封当。
待信使策马出城,身后竟跟随着数万流民。
众人离去后,修县街道顿显宽敞。
-----------------
又越三日,张旸率部巡城。
行至半途,只见封当汗流浃背,踉跄奔至营中,高声呼道:
“将军!将军!”
张旸闻言,眉头紧锁,回身欲斥。
封当却抢先一步,大声禀报道:
“将军,元皓先生归矣!”
张旸听闻,原本愠怒之色瞬间消散,急道:
“速引我去!”
闻田丰归来,张旸无心再巡,遂留半数亲卫代行巡察,自己则与封当奔赴田家。
至其宅邸,方知田丰居于城郊田庄。
田家众人闻张旸等人来意,不敢懈怠,即刻备车,护送众人前往。
途中,张旸掀开帘幕,见修县街市井然有序,颔首赞道:
“甚好!此番流民离去,修县倒添几分清净。”
封当眯目抚须,笑道:
“将军所言极是。修县地狭,实难容纳众多流民。如今南皮缺人,恰可互通有无。”
张旸微微挑眉,放下帘幕,说道:
“修县地处五郡交界,乃渤海之要冲。日后当扩建城郭,方能稳固渤海门户。”
封当听闻,大笑道:
“若能在我任内得见新修县,也算留名青史了。”
张旸摆手笑道:
“伯轩莫作此想。修筑一城,何足留名?汝但随我,日后必能扬名天下!”
封当闻言,心中畅快。
近日来,他办事顺遂,全因张旸将政务放权于他,仅每周军政议事时,派人审查政事。
在黄巾军制的框架下,辅兵维持秩序,封当诸事顺遂,再无掣肘之苦。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修县大族对他暗生嫉妒。
封当想起冀家主的酸言酸语,不禁暗自好笑。
张旸见封当一路含笑,欲问又止。
不多时,众人抵达田庄。
下车后,张旸对封当道:
“汝与元皓先生相熟,烦请代为引见。”
封当点头,上前叩门三声,朗声道:
“元皓先生,我乃伯轩。听闻先生自安平国归来,特来拜见!”
片刻后,庄门微启,一老叟探出头来。
见是封当,老叟开门笑道:
“封家主,请进。”
封当引张旸入内,跟随老叟穿过几道水榭,来到一处小亭前。
只见一人正在亭中垂钓。
老叟拱手告退,封当回礼后,向张旸示意:
“将军,此人便是元皓先生。”
张旸点头笑道:
“果有不凡之气。伯轩,速为我引见。”
封当欣然伸手:
“将军请。”
二人快步来到亭前。
封当立即向亭中清瘦男子行礼:
“元皓先生,封当前来拜见!”
田丰赶忙起身回礼。
礼毕,他看向封当,又斜目扫了张旸一眼,问道:
“伯轩,许久不见。黄巾可曾为难城中百姓?”
封当瞧了张旸一眼,见其未作表示,便摆手笑道:
“正如先生所料,张将军治军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
田丰点头,转而看向张旸,问道:
“这位兄台是?”
封当正要介绍,张旸抬手制止:
“伯轩不必多言,元皓先生想必已认出我。张某冒昧前来,还望先生勿怪。”
田丰见张旸豪爽且不失礼数,拱手笑道:
“张将军光临寒舍,蓬荜生辉。还请让我略尽地主之谊。”
张旸亦拱手回礼:
“如此甚好。我正欲与先生、伯轩兄共商渤海诸弊,寻求解决之策。”
田丰抚须朗笑,袍袖一摆,抬手向亭内引道:
“二位,请。”
三人甫一落座,下人便端上茶汤糕点,热气腾腾。
封当与田丰相交久矣,毫无拘谨,径自拍案而起,抓起一块糕点,大快朵颐。
吃罢,转头向张旸笑道:
“将军,元皓先生府上这糕点,滋味一绝,我每次来都必尝,将军不妨一试!”
田丰见状,非但不恼,反倒向张旸拱手示意:
“将军,请。”
张旸颔首致谢,取过一块糕点放入口中,只觉滋味爽口,当即赞道:
“果然好味!”
田丰笑容愈盛,亦取糕点,轻咬一口,品味片刻后,缓缓说道:
“此糕用料繁杂,需以小火慢烘,耗时颇久,稍有差池,便前功尽弃,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才有这般滋味。”
言罢,目光灼灼地看向张旸,问道:
“将军觉得,这做糕之法,与治理渤海郡,可有几分相似?”
张旸正襟危坐,虎目澄澈,嘴角含笑:
“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天下,自然需慢工出细活。我研习黄老之术,主张与民休息,循序渐进。不过,此道只适用于太平盛世,先生以为呢?”
田丰双眼微眯,目光如炬,细细打量张旸。
此前便听闻他乃张良后人,今日一番对答,看来所言非虚。
心中已有计较,田丰不再试探,直截了当地问道:
“那将军认为,黄天之道,以小民之利为先,乃至撼动权贵,便可迎来盛世?”
张旸微微仰头,虎目似燃烈火,言辞铿锵:
“正是!民为邦本,唯有小民富足,国家方能真强盛。一代又一代贤能之士,与小民齐心协力,定能实现天下大同。或许我此生无法得见,或许会遭遇失败,但只要踏出这一步,后人便可引以为鉴。我愿为后世开辟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