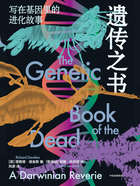
第1章 阅读动物
你是一本书,是一部未完成的文学作品,也是一份述说历史的档案。你的身体和你的基因组可以作为一份综合档案来加以解读,其中记载了一系列早已消失的多彩世界,那些早已逝去的你的祖先所身处的世界。每个个体都是一本“遗传之书”。对于每一种动物、植物、真菌、细菌,乃至古生物而言,事实莫不如此,但为了避免对各种生物所属类别进行令人厌烦的重复说明,我有时会将所有生物视为“名誉动物”。我对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说过的一句话记忆犹新,他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与我英雄所见略同。当时我们由一位在巴拿马丛林工作的史密森学会科学家带领一同参观丛林,梅纳德说道:“聆听一个真正热爱他的‘动物’的人的介绍真是一种享受。”而他在这里所说的“动物”其实是棕榈树。
从动物的角度来看,根据“未来不会与过去大相径庭”这一合理假设,“遗传之书”也可以被视为对未来的预言书。还有第三种对其加以描述的方式,也就是某种动物(包括其基因组)是过去环境的某种具现化的“模型”,它利用自身这个模型有效预测未来,从而在这场“达尔文主义的游戏”——生存繁衍的游戏,或者更准确地说,基因生存的游戏——中取胜。动物的基因组打赌,它所面对的未来与它的祖先成功应对的过去不会大相径庭。
我刚才说,动物可以被当作一本关于过去世界——它祖先所处的世界——的书来阅读。我为什么不说动物可被当作关于它自身所处生活环境的书来阅读呢?它的确也可以这么解读,但是(一些保留意见有待讨论),动物生存机制的方方面面都是其祖先在自然选择作用下通过基因遗传得到的。因此,当我们解读动物时,实际上是在解读“过去”的环境。这就是为什么英文版书名中包含“dead”(去世的)。我们所谈论的是复原一个远古世界,我们那些早已逝去的祖先在那个世界里生生不息,并由此将塑造我们现代动物的基因代代相传。目前,这种复原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未来的科学家如果面对一种迄今未知的动物,会有能力将其身体和基因作为对其祖先生活环境的详细描述来加以解读。
在书中,我将经常求助于我想象中的“未来科学家”(Scientist Of the Future),她面对的是一具迄今未知的动物的尸体,承担的任务则是读懂它。因为我需要经常提到她,为了简洁起见,我将称她为SOF。它与希腊语中的“sophos”一词有微妙的共鸣。sophos意为“智慧”或“聪明”,如在“philosophy”(哲学)、“sophisticated”(见多识广)等词中,它均作为词根出现。为了避免笨拙累赘的代词结构,也是出于礼貌,我武断地假定SOF为女性[1]。如果我碰巧是一位女作家,那我就会假定其为男性。
这本“遗传之书”,这本从动物及其基因中“读出”的书,这本对祖先环境的丰富编码的描述,必然是一本“重写本”(palimpsest)。一些古代文献的一部分会被后世叠加其上的文字覆盖,这就是所谓的“重写”。《牛津英语词典》对“重写本”的定义是:“一种将后来的文字叠加在早期(被抹去的)文字之上的手稿。”我已故的同事比尔·汉密尔顿(Bill Hamilton)有一个有趣的习惯,就是以重写本的方式来写明信片,并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来减少混淆。他的妹妹玛丽·布利斯(Mary Bliss)博士好心地把下图借给我当作例子使用。

在这里之所以以汉密尔顿教授的明信片为例,除了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份漂亮的彩色重写本之外,还因为汉密尔顿教授被公认为他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达尔文主义者[2]。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在悼念汉密尔顿时说:“他拥有我所见过的最微妙、最富有层次的思想。他说的话往往有双重甚至三重含义,也就是说,当我们其他人在用单个音符说话和思考时,他却用和弦思考。”[3]或者,在这里应该换个比喻,说他用“重写本”的方式思考。不管怎么说,我想他会喜欢“进化重写本”这个概念的。事实上,他应该也会喜欢“遗传之书”这个概念。
不管是汉密尔顿的明信片,还是我所谓的“进化重写本”,都不符合词典中对“重写本”的严格定义,因为这两个例子中的早期“文字”并没有被不可挽回地抹去。在“遗传之书”中,它们被部分覆盖,但仍然可以阅读,尽管我们必须“透过模糊的玻璃”[4],或透过一堆后来书写其上的文字,才能对这些原始文字加以窥探。“遗传之书”所描述的环境肇始于前寒武纪的海洋,跨越亿万年,历经无数中间阶段与事物,直至近世以降。据推测,其中的“现代字迹”与“古代字迹”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我认为,这并不像某些宗教处理宗教经典中自相矛盾的经文那样遵循一个简单套路——新的总是胜过旧的。我将在第3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你就必须做出预测,或者表现得好像在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有明智的预测都必须以过去为基础,而且许多这样的预测都是统计性的,而不是绝对性的。有时,这种预测是认知性的——“我预见到,如果我掉下悬崖(或抓住那条蛇咔咔作响的尾巴,或吃下那些诱人的颠茄果),很可能会因此遭受痛苦乃至一命呜呼”。我们人类习惯于这种认知性预测,但它们并不是我心目中的预测。我更关心的是无意识的、统计性的“假设性”预测,即对什么可能会对动物未来的生存及其基因副本传递下去的机会有所影响的预测。
右页图中这只栖息在莫哈韦沙漠的角蜥,其皮肤的颜色和花纹酷似沙子和小石头,它的基因预示着它会在沙漠中出生(更确切地说,是孵化)。同样,动物学家在看到这只蜥蜴时,也能将它的皮肤作为对其祖先所生活的沙漠环境中的沙砾的生动描述进行解读。现在我要表述的中心思想是,可以拿来解读的不仅仅是皮肤,动物的整个身体,它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生化过程,以及每一个动物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包括它的基因组,都可以被解读为对其祖先世界的描述。就角蜥而言,毫无疑问,它的整个身体和皮肤一样都是对沙漠的描述。“沙漠”一词将被写入这种动物的每一个部位,但一同被写入的还有更多关于其祖先的信息,这些信息远远超出了当今科学所能获得的范畴。

角蜥从卵中破壳而出的时候,它被赋予的基因预言是,它将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阳光普照、遍地沙砾的世界里。如果它违背了自己的基因预言,比如从沙漠误入高尔夫球场,一只路过的猛禽很快就会把它叼走。或者,如果世界本身发生了变化,以至于它的基因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它也很可能会遭到灭顶之灾。所有有用的预测都取决于一点:未来与过去大致相同,至少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如此。一个反复无常的世界,一个随机变化、难以预料的混乱环境,将使预测变得不可能,并因此危及生存。幸运的是,这个世界是保守的,基因可以安全地下注,预测任何地方的既有趋势都会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当然,在有些情境下,预测也会失败,比如在灾难性的洪水或火山爆发后,再或者在像小行星撞击导致恐龙悲惨谢幕这样的情况下,这时所有的预测都难免错谬,所有的赌注都被一笔勾销,整个动物群体灭绝。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面对的不是这样的大灾难:不是动物界中的大量物种被一举消灭,而只是那些预测稍有差错的变异个体,或者相比同类竞争者的预测差错更多的变异个体会遭逢灾厄。这就是自然选择。[5]
重写本最上层的字迹是最近才写就的,是用一种特殊的文字,在这种动物自己的一生中写成的。自动物出生以来,基因对祖先世界的描述就被各种修改和对细节的完善覆盖——动物从经验中学习并据此书写或覆写,其内容或许是免疫系统对过去疾病的深刻记忆,或许是生理上的适应,比如对海拔的适应,甚至可能是通过对未来可能结果的模拟而写就的。这些最新的字迹并不是由基因传递下来的(尽管书写它们所需的设备是),但它们仍然相当于来自过去的信息,也可用来预测未来。只是这些字迹代表的是最晚近的过去,是动物自己一生中经历的过去。第7章讲述的便是关于自动物出生以来就被潦草地写进这个重写本里的那些部分。
最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动物的大脑会为变动不居的环境建立一个动态模型,实时预测变化。在康沃尔海岸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正羡慕地看着海鸥在利泽德半岛的悬崖峭壁上方乘风翱翔。每只海鸥在飞翔时,其翅膀、尾羽,甚至头部的角度,都在根据不断变化的阵风和上升气流进行灵敏的自我调整。想象一下,SOF,我们未来的动物学家,在一只海鸥的大脑中植入了通过无线电相连接的电极。她可以借此获得海鸥肌肉调整的相关数据,而这将转化为对风涡流的实时连续解析:鸟类大脑中的预测模型可以敏感地微调其飞行面,以便将其带入下一个飞行瞬间。
我说过,动物不仅是对过去的描述,也不仅是对未来的预测,它还是一个“模型”。什么是模型?等高线图是一个国家的地理模型,你可以根据这个模型复原该国地貌,并在其中穿行。计算机中的“0”和“1”组成的列表也是如此,它是地图的数字化呈现,或许还包括与之相关的信息:当地人口数量、种植作物、主要宗教等等。按照工程师的理解,任何两个系统都是彼此的“模型”,只要它们的行为具有相同的基础数学架构。你可以用连接电线的方式组装出一个钟摆的电子模型。钟摆和这个电子振荡器的周期都由同一方程决定,只是等式中的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不同而已。数学家可以将它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连同写在纸上的相关方程,视为另外那个的“模型”。天气预测者构建的是一个世界天气的动态计算机模型,该模型通过放置在适当位置的温度表、气压表、风速表以及如今最重要的卫星所提供的信息不断更新。这个模型可以运行到未来,对世界上任何选定的地区进行天气预测。
感觉器官并不会将外部世界的“电影”忠实地投射到大脑内的小电影院中。[6]是大脑构建了外部真实世界的虚拟现实(VR)模型,且这个模型通过感觉器官不断更新。就像天气预测者通过计算机模型预测未来的天气一样,每种动物每时每刻都在用自己的世界模型预测未来,并以此指导自己的下一步行动。每个物种都建立了自己的世界模型,这种模型以对该物种的生活方式有益的形式呈现,对预测其如何生存至关重要。不同物种的世界模型肯定相去甚远。燕子或蝙蝠头脑中的模型必然近似于一个由快速移动的目标组成的三维空中世界。至于这个模型的更新是依据眼睛的神经冲动,还是依据耳朵的神经冲动,也许并不重要。神经冲动就是神经冲动,无论其来源为何。松鼠的大脑必然运行着与松鼠猴相似的VR模型。两者都必须在由树干和树枝组成的三维迷宫中穿梭腾挪。牛的模型更简单,更接近二维。青蛙并不像我们理解世界那样塑造整个场景。青蛙的眼睛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向大脑报告正在移动的小物体[7]。这种报告通常会引发一连串的刻板行为:转向目标、跳跃以靠近目标,最后将舌头射向目标。青蛙眼睛的预设线路也体现了一种预测,即如果青蛙朝指定方向伸出舌头,就有可能命中食物[8]。
我那生活在康沃尔郡的祖父在马可尼公司成立初期曾受聘于该公司,向进入公司的年轻工程师传授无线电原理。在他的教学辅助工具中,有一根晾衣绳,他会把它摆荡起来,作为声波或者无线电波的模型,因为同样的模型适用于两者。这就是重点所在。任何复杂的波——声波、无线电波,甚至是一波海浪——都可以被分解成正弦波分量,这就是“傅里叶分析”(Fourier analysis)[9],以法国数学家约瑟夫·傅里叶(Joseph Fourier,1768—1830)的名字命名。反过来,这些正弦波又可以再次求和以重建原始复合波,即“傅里叶合成”(Fourier synthesis)。为了证明这一点,祖父会把晾衣绳的两头系在旋转的轮子上。只有一个轮子转动时,绳子会产生近似正弦波的蛇形波。而当两个轮子同时旋转时,绳子的蛇形波变得更加复杂。正弦波的和是对傅里叶原理的一个基本而生动的演示。祖父的蛇形晾衣绳是无线电波从发射机传播到接收机的模型,也可以是一种进入耳朵的声波的模型:大脑在分析这种复合波时,可能会对其进行相当于傅里叶分析的操作,例如,即使是管弦乐队正在演奏,人耳依然能分辨出耳语和烦人的咳嗽声这样的复杂模式。令人惊奇的是,人类的耳朵,实际上是人类的大脑,可以从整个管弦乐队的复合波形中,分辨出双簧管和法国号(圆号)各自不同的音色。
今天,我祖父的同行会用电脑屏幕来代替晾衣绳[10],先让屏幕显示一个简单的正弦波,然后显示另一个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再将两者相叠加,生成一个更复杂的摆动线,诸如此类。下图是我说出一个英语单词时的声音波形图——高频的气压变化。如果你知道如何分析它,从这张(放大了很多倍的)图片所包含的数值数据就能读出我说了什么。事实上,你需要大量的数学智慧和计算机功率才能破译它。但是,只要把这条摆动线制成老式留声机唱针所扫过的相应唱纹凹槽,由此产生的气压变化波就会轰击你的耳膜,并在与你大脑相连的神经细胞中转化为脉冲模式。然后,你的大脑就会毫不费力地实时进行必要的数学运算,从而识别出“姐妹”(sisters)这个词。

我们大脑中的声音处理软件可以毫不费力地识别口语,但当我们面对记录在纸上、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的波浪线,或者组成这条波浪线的数字时,我们的视觉处理软件却极难将其破译。尽管如此,所有的信息都包含在这些数字中,无论它们是如何呈现的。要破译它,我们需要借助高速计算机进行明确的数学计算,而且计算难度很大。然而,如果以声波的形式呈现相同的数据,对我们的大脑而言,这种破解却轻而易举。这是一个寓言故事,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这对本书主旨而言至关重要,所以我不惜在此重复一遍——动物的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难“读懂”。莫哈韦角蜥背上的花纹很容易解读:难度相当于听到“姐妹”的发音。显然,这种动物的祖先是在多沙石的沙漠中谋求生存的。但是,我们也不应在困难的读取任务面前退缩,比如说肝脏的细胞化学。这可能很难,就像在示波器屏幕上看到的“姐妹”对应的波形一样。但这并不能否定一个重点,那就是无论多么难以破译,信息都潜藏在其中。“遗传之书”可能会像线形文字A或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一样高深莫测。但我相信,信息就蕴藏其中。
右侧的图案是一个二维码。它包含一条隐藏信息,人眼无法读取,但你的智能手机却能立即破译。如果你用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屏幕上会立刻显示出我最喜欢的诗人的一句诗。“遗传之书”是隐藏在动物身体和基因组中的关于其祖先世界信息的重写本。就像二维码一样,它们大多无法用肉眼读取,但未来的动物学家们将能够利用先进的计算机和其他工具来读取它们。

重复一下我的中心论点,当我们观察一种动物时,在某些情况下(莫哈韦角蜥的例子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可以立即读出其祖先生存环境的具体描述,就像我们的听觉系统可以立即破译口语中的“姐妹”一词一样。本书第2章中就考察了那些几乎是把祖先生存环境直接画在背上的动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必须采用更间接、更困难的方法来获得读数。后面几章将介绍一些可行的方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技术目前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尤其是那些涉及读取基因组的技术。我写本书的部分目的也在于激励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分子遗传学家以及其他比我更能胜任的学者去开发这样的方法。
首先,我需要消除读者对书名(本书的英文书名可直译作《亡者的基因书》)可能产生的五个误解。第一,令人失望的是,我并未破译这本“遗传之书”的大部分内容,而是寄希望于未来的科学研究。对此我也无能为力。第二,除了一种富有诗意的共鸣之外,我这本书与古埃及的《亡灵书》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古埃及的《亡灵书》都是死者的陪葬品,是帮助他们迈向永生的指导手册。而动物的基因组同样是一本指导手册,为动物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指明路径,并以这样一种方式将手册(而不是躯体)传递到不确定的未来,即使那并非真正的永生。
第三,我的书名可能会让读者误以为本书是关于“古DNA”(Ancient DNA)这一引人入胜的主题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获得逝去已久的生物——不幸的是,并不是太久远的生物——的DNA,但往往是支离破碎的片段。瑞典遗传学家斯万特·佩博(Svante Pääbo)因拼凑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而获得诺贝尔奖[11],若非如此,我们只能从零星化石中对这些物种有所了解,而目前仅发现了丹尼索瓦人的3颗牙齿和5块骨头碎片。佩博的工作也顺带表明,欧洲人,而非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是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罕见混种的后裔。此外,一些现代人,尤其是美拉尼西亚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智人与丹尼索瓦人的杂交事件。目前,古DNA研究领域正在蓬勃发展。长毛猛犸象的基因组几乎已被我们完全了解,人们对该物种的复活抱有很大期望。其他可能复活的物种还包括渡渡鸟、旅鸽、大海雀和袋狼(塔斯马尼亚狼)。[12]遗憾的是,完整足量的DNA最多只能保存几千年。无论如何,古DNA虽然饶有趣味,但并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
第四,我不打算比较不同现代人类种群的DNA序列,也不打算探讨它们对历史的启示,包括席卷地球陆地表面的人类迁徙浪潮。这些基因研究与语言之间的比较重叠,颇为引人入胜。例如,基因和词汇在西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的分布情况表明,岛屿间距离和词汇相似度之间存在数学上的规律性关系。[13]我们可以想象,满载着基因和词汇的独木舟在开阔的太平洋上疾行是怎样的场景!但那将是另一本书中的一章。也许那本书的书名就叫《自私的模因》(The Selfish Meme)。
第五,本书的书名不应被理解为现有科学已经可以将DNA序列转化为对古代环境的描述。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也不清楚SOF能否做到这一点。本书的主题是解读动物本身,以及它的身体和行为——表型(phenotype)。过去的描述性信息是通过DNA传递的,这是事实。但目前我们是通过表型来间接解读它们的。将人类基因组转化为一具可运作躯体的最简单的,甚至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将其输入一种名为“女性”的特殊解读装置中。
作为雕像的物种;作为求平均值计算机的物种
堪称博学多才的动物学家、古典学家兼数学家达西·汤普森爵士(Sir D’Arcy Thompson,1860—1948)[14]曾说过一句话,这句话看似老生常谈,甚至有些同义反复,实际上却引人深思:“万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成了如此。”太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物理规律将一团气体和尘埃发展成了一个旋转的圆盘,后者随后凝结成太阳,再加上在同一平面内沿同一方向旋转的天体,它们标志着最初圆盘的平面。月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45亿年前地球遭受了一次剧烈的撞击,大量物质被抛入轨道,然后在重力的作用下被拉扯、揉捏成一个球体。月球的旋转速度慢于其最初速度,这是一种叫作“潮汐锁定”(tidal locking)[15]的现象,因此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个面。更多的轻微天体撞击使月球表面布满了陨石坑。如果没有侵蚀作用和板块运动,地球表面也会坑坑洼洼。至于雕像,一件雕像之所以呈现如此形态,则是因为一整块卡拉拉大理石得到了米开朗琪罗的精心雕琢。
那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是现在这个样子?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月球一样,我们身上也有着外来损害留下的伤疤——枪伤,决斗者的军刀或外科医生的手术刀留下的纪念性疤痕,甚至是天花或水痘造成的“微小陨石坑”。但这些都是细枝末节而已。身体主要是通过胚胎发育和生长过程形成的。而这些过程又是由细胞中的DNA引导的。那么DNA又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这下我们说到点子上了。每个个体的基因组都是这个物种基因库的一个样本。基因库经过许多代的进化而形成,其部分是通过随机漂变,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个非随机“雕刻”的过程。这位“雕刻家”便是自然选择,它以无形的斧对基因库进行雕琢和修削,直到后者——以及作为其外在和可见表现的躯体——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说经受“雕刻”的是物种基因库,而不是个体的基因组呢?因为,与米开朗琪罗的大理石不同,个体的基因组不会改变。个体基因组不是雕刻家雕刻的实体。一旦受精,基因组就会固定下来,从卵子到胚胎发育,再历经童年、成年和老年,一成不变[16]。在达尔文式斧凿下发生变化的是物种的基因库,而不是个体的基因组。[17]将这种变化称为“雕刻”是恰如其分的,因为由此产生的典型动物形态呈现出一种演进趋势。所谓演进,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形态像罗丹或伯拉克西特列斯的作品那样更加美丽(尽管通常如此)。这只是意味着动物在生存和繁殖方面表现得更好。有些个体能存活下来繁衍后代,另一些则英年早逝;有些个体有很多配偶,另一些则孑然一身;有些个体子嗣断绝,另一些则膝下儿女成群。性重组确保了基因库被不断搅动和震荡。基因突变则将新的基因变异投入混杂的基因库中。而自然选择和性选择会使世代相传的物种平均基因组的塑造朝着建设性的方向演变。
除非我们是群体遗传学家,否则我们无法直接看到被雕刻的基因库发生的变化。相反,我们观察到的是物种成员平均身体形态和行为的变化。每个个体都是从现有基因库中提取的基因样本,并通过合作的方式培育出来的。一个物种的基因库就是一块不断变化的大理石,自然选择这套精细、锋利、精巧、深入的斧凿在这块大理石上切削雕琢着。
地质学家观察一座山脉或一个山谷,然后对其加以“解读”,复原其从远古到近代的历史。山脉或山谷的自然雕琢可能始于火山喷发,或地质构造的俯冲和隆起,然后再经历风霜雪雨、河流冰川的侵蚀凿刻。而当生物学家观察化石历史时,她看到的不是基因,其目之所能及的,是平均表型的渐进变化[18]。但是,真正经历自然选择雕刻的实体却是物种基因库。
有性生殖的存在赋予了“种”(species)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这是分类学中其他单位——属、科、目、纲等——所不具备的。为什么?因为基因的有性重组——洗牌——只发生在种内。这正是“物种”的定义。这就引出了本节标题中的第二个隐喻:物种是一台求平均值的计算机。
“遗传之书”是对祖先个体所处世界的书面描述,其中没有哪一个个体相比另一个更为突出。这本书是对塑造了整个基因库的环境的描述。我们今天所研究的任何个体,都是从被洗牌、被振荡、被搅动后的基因库中提取的样本。而每一代的基因库都是统计过程的结果,是物种内所有成功和失败的个体的平均值。所以说,物种就是一台求平均值的计算机,而基因库就是它赖以工作的数据库。
[1]性别代词几乎注定会冒犯某些人。我不喜欢诸如“他或她必须扪心自问,让他或她或他们接受如此折磨人的语言,对读者是否公平”这样费力的结构。在许多语言中,甚至连“读者”(reader)这个词都可能要写双份:“Leser oder Leserin?”(男读者或者女读者?)我赞成另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就像吻手礼或旧世界的屈膝礼一样,作者采用与自己性别相反的性别代词。因为我碰巧是男性,所以我把我假想的未来科学家称为“她”。如果我是女作家,我会反其道而行之。
[2]参见汉密尔顿在自传《基因之地的狭窄道路》(Narrow Roads of Gene Land,三卷本)中所做的尝试,他在个人回忆录中那些袒露心灵的文章之间插入了重印的技术性科学论文。“所以我最后一次坦白。如果有人能说服我相信‘长生不老药’有望研制成功,我可能也会因为对死亡的怯懦而为‘长生不老药’和老年学研究提供资金。但同时,我也不愿意抱有这样的希望,免得我受到诱惑。在我看来,长生不老药似乎是一种最糟糕的反优生愿望,它无法创造一个我们的后代可以安享的世界。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做了个鬼脸,屈起一根仍然可以与其他手指轻松合作的拇指,揉了揉两道不请自来的浓密眉毛,从鼻孔里哼了一声——鼻孔里的鼻毛长得越来越像爱德华时代的旧沙发上的一簇簇马毛——我俯下身时,指关节已碰不到地面,尽管几乎碰到了。我继续奋笔疾书,写我的下一篇论文。”
[3]Trivers(2000).
[4]化用自《圣经·哥林多前书》(13∶12),原文为“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这个尾注本来是不必要的。这句话是我在《上帝的错觉》(The God Delusion)一书中列出的129个《圣经》短语之一,就像莎士比亚的许多短语一样,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国家是充实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必要知识储备。我支持宗教教育,是指我支持关于宗教的教育,而不是某种宗教的灌输。
[5]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是在种群内选择,而不是在种群之间选择。达尔文对此非常清楚[除了在1871年《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中谈到人类时的一次例外]。恐龙被哺乳动物取代,但这种取代不是达尔文式的选择事件。真正的达尔文意义上的选择事件,是每个哺乳动物物种中个体的生存差异,其反映了个体在填补某些特定的已灭绝恐龙物种留下的空缺这一事业中取得的成功。
[6]“笛卡儿剧院”(身心关系模型)里没有一个小人(Dennett, 1991)。
[7]莱特文等人(Lettvin et al., 1959)接着测量了青蛙在看到物体时大脑中单个神经元会产生怎样的神经冲动。例如,当出现一个小的移动物体时,“同一性”神经元最初是沉默的。然后,突然,它“注意到”这个物体并开始激发神经冲动。每当物体改变其运动模式,例如转弯时,激发速率就会增加。
[8]生理学家贺拉斯·巴洛(Horace Barlow, 1961, 1963)在青蛙的视觉系统方面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对一般的感觉系统有一个鼓舞人心的看法,这与本书主旨非常吻合。他将神经表征总结为“对当前环境可能真相的近似估计”。他没有这么说,但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动物的感觉系统的调节方式是对其所处世界的统计特性的一种消极描绘。
[9]有一次,在克鲁格国家公园,我偶然发现了一只发情期的公象在尘土中留下的尿迹。它看起来近似正弦波,显然是它那滴尿的阴茎像钟摆一样摆动造成的。我拍下它的时候,脑子里出现了模糊的念头:找个数学家对此进行傅里叶分析,然后计算出这头象的阴茎长度。就像我的许多计划一样,它从来没有实现过。
[10]计算机模拟为建模提供了一种特别有用的工具。计算机内部除了以极快的速度传输数十亿个0和1之外,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计算机的数据可以代表一个棋局、世界天气、伯明翰复式公路枢纽的交通模式、钟摆、《英雄交响曲》、旅鼠和北极狐的种群周期、温哥华市,或心脏肌肉纤维收缩产生的波动。
[11]在我看来,佩博和他的同事们还应该因为他们严谨、认真地制定古DNA研究的方法而受到表彰。这个领域的陷阱既多又深,首要的就是现代DNA的污染。由于此前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世界各地有许多荒谬的关于古DNA的草率头条报道。
[12]要复活灭绝的哺乳动物,就引出了如何在现存动物中寻找替代子宫的问题。大海牛的DNA已被复原。如果能让它们起死回生,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一个可能无法克服的问题是上哪儿找一个代孕母亲并为其植入胚胎。大海牛现存的近亲儒艮和海牛的体型都太小了,无法生下大海牛。在这方面,复活猛犸象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幸存的大象足够大,可以孕育猛犸象。有趣的是,复活有袋动物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它们出生时非常小,会爬进育儿袋继续发育。找一个替代的育儿袋比找一个替代的子宫要容易得多。一只拉布拉多犬大小的塔斯马尼亚狼,即袋狼,在出生时应该只有米粒那么大,和它幸存下来的只有老鼠大小的亲戚——狭足袋鼩——刚出生时大小相近。在遥远的未来,胚胎学家可能能够在子宫外培育胚胎。DNA的数字化本质之美,在于无须保存任何实际的生物材料。这些未来的胚胎学家只需要去图书馆下载基因组即可。
[13]Cavalli-Sforza & Feldman, 1981.
[14]《生长与形态》(On Growth and Form,1942)是汤普森的文笔优美的巨著,其中引用了许多语言的语录,包括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普罗旺斯语,通常没有翻译——除了普罗旺斯语,他确实为我们翻译(成法语)了。我感谢丹尼斯·诺贝尔证实了书里那段普罗旺斯语引文出自伟大的博物学家让-亨利·法布尔(Jean-Henri Fabre)的一首诗。它促使汤普森写下了令人心酸的一段旁白,描述了一个老人与地心引力所做的斗争。“但在某种程度上,身高的缓慢下降表明我们的体力与不变的重力之间存在不平等竞争。当我们想站起来的时候,重力却把我们拉下来。我们一生都在与重力做斗争,在我们四肢的每一次运动中,在我们心脏的每一次跳动中,斗争不曾停歇;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力量最终打败了我们,让我们僵卧在临终的榻上,将我们送入坟墓。”我之所以说“令人心酸”,是因为爵士在壮年时期,用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的话来说,“身高超过六英尺,有着维京人的身材和举止,以及众所周知的英俊外表所带来的傲气”。
[15]天体物理学中的一个现象,指的是一个较小的天体(如卫星)的自转周期与其绕较大天体(如行星)的公转周期达到同步的状态。在潮汐锁定的情况下,较小天体始终以同一面面向较大天体,这种现象是潮汐力导致的。——译者注(以下若无特殊说明,脚注均为译者注)
[16]嗯,几乎完全不变。在某些方面,我们需要这个“几乎”,但这对于本章的观点来说并不重要。“体细胞”突变,即体内细胞的突变,确实会发生,它们可能会产生在体内进化的细胞系。伴随着更多体细胞突变,可能会产生肿瘤。对这些体内叛逆细胞的自然选择可以将肿瘤变成恶性肿瘤。之后,这种选择会使它们变得更善于恶变——但对整个身体来说却适得其反。我们将在第12章再讨论这个问题。出于本章的目的,我们在此只关心所谓种系中的突变,即可能遗传给后代的突变。
[17]人们很容易把“进化”和“发育”混为一谈。在发育过程中,单个实体会发生变化。而在进化过程中,一系列实体中的每一个都与其前身略有不同,就像电影的连续帧一样。天文学家说恒星沿着“主序进化”是错误的,例如“太阳最终进化为一颗红矮星”。太阳并没有连续世代。只有一个太阳发生了变化。不,应该说,太阳经过发展(发育),最终会形成一颗红矮星。我们看到生命体的形状是通过胚胎学的过程发育形成的。当我们把连续几代动物按顺序排列,观察其典型形状是如何一代一代地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身体形状是如何演变的。一个物种的典型成员的形状随着基因库的发展而进化。
[18]进步主义圈子里的生物学家应该对进化论是进步主义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如果是针对“‘进化’旨在努力达到所谓智人的巅峰”这种对进化的通俗化夸张描述加以怀疑,那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谈论像眼睛这样的复杂器官的进化时,你无法摆脱“渐进式改进”的概念。功能完备的脊椎动物的眼睛,必然要经过一系列效率较低的中间阶段,这是逻辑上的必然。迈克尔·鲁斯(Michael Ruse, 2010)对进化论中渐进观点的历史做了很好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