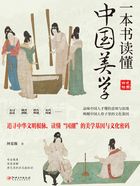
第一节 原始审美意识的发生
讲述中国美学,总要有个起点。那么中国美学的起点在哪儿呢?在原始社会。这时候中国美学思想并未产生,但了解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原始审美意识是如何产生的,有利于正确把握中国古代社会审美观念的发展特点。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祖先在实践活动中逐步孕育了早期的审美意识,原始艺术得以产生。这种原始艺术大多是由物质实践的产物转化而来,强调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结合。我们现在所说的审美意识,一般没有也不能具有实际的功利目的,它体现为人的自由的精神需要,精神愉悦或灵魂净化。也就是说,美是无功利、无利害、没有实际目的、拒绝物欲的。然而,这审美的“无功利”却是以“有功利”为历史前提与心理前提的。在人类漫长的文化历程中,原始先民在实践中总是带有生存目的,包含求生欲望、欢乐或痛苦的自我意识、情感因素等,它是实用的、物欲的。因此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原始艺术的载体(陶器、玉器、岩画等),往往带有趋吉避凶的目的性。除此之外,原始艺术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具有原始思维的特征,它与神话、图腾、巫术等密切相关。
所谓神话,诸如后世传说中的女娲补天、伏羲画卦、仓颉造字、神农尝百草、后羿射日以及大禹治水之类,这些都是富有原始思维的神话。由于各种族、民族的人种体质及其所生活的环境各有不同,因此生成各自的“种族记忆”,产生了各种远古神话,其中包含了诞生、死亡、再生、力量、英雄、巨人等审美“原型”。
所谓图腾,是从印第安语翻译而来,是古代原始部落信仰某种自然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等,并将其作为本氏族的徽号或象征,也是原始初民早期的宗教信仰之一。图腾是一种史前文化的“错觉”,它将动植物、山岳、河川之类认作氏族的“先父”或“先母”,以便使整个氏族牢固地团结在“图腾”的旗帜下,去共同面对外部世界与恶劣环境的挑战。图腾使一个民族的精神有一个参照可以依附,使人们共同沐浴在这个偶像崇拜的文化氛围中。中国古籍关于原始图腾及其文化遗构的记载很多。《诗经·商颂》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商部落原以“玄鸟”为图腾。《山海经》所言“人面蛇身”“人首蛇身”,两汉时期《淮南子》记载“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还有南宋学者罗愿所谓“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之龙的形象,实际是多种动物图腾的综合,证明中国原始图腾的崇拜对象十分丰富。在中国的广袤大地,还有以蛙、鱼等作为图腾的。但总的来说,龙与凤的形象源远流长,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审美的根源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美的象征。
神话与图腾中所反映的原始生命意识、“天人合一”观念、“象”意识等,与原始社会人们长期的穴居生活、生产方式有一定的关联,是中国审美意识的萌芽。除了女娲、伏羲的传说,我们从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彩陶盆、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龙虎蚌塑(用蚌壳摆塑的龙和虎的形象)、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以及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凤等古物中,都可以看到神话、图腾影响下人们的原始思维和审美观念。
当然,原始文化“原始混沌”,万物往往并不是分立、分开的,如中国的龙,既是中国文化之最显著、最重要的“原始意象”,是神话之原型,又是中华民族生殖、崇祖的图腾崇拜,它同时还与原始巫术文化联系在一起,表示某种征兆。我们所知道龙虎蚌塑、战国帛画《人物御龙图》中的龙,可能带有引魂升天或某些巫术色彩。如果说神话与图腾是偏重于从原始人类的文化心理、观念来研究原始审美意识的话,那么巫术是以原始人类的文化实践方式来加以考察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原始巫术几乎渗透、贯穿于原始初民的一切生产与生活领域,它是原始初民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策略,也是原始初民与自然力量进行“对话”的主要方式。盛于殷商的甲骨占卜、商周之际的《周易》筮占,以及《左传》《国语》等典籍关于卜筮的丰富资料记载,都证明原始巫术文化曾在中国盛行,它历史地酝酿着属于这个伟大民族的独特的原始审美意识。中国古代的“史”是由“巫”发展而来的,因此,原始审美意识的发生可能与巫术有着更为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
夏、商、周的审美观念是在原始审美意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原始社会神权与王权的合一、巫与政的合一,在夏、商、周时期得到继承并进一步细化,产生了兽形神的崇拜、饕餮的狰狞恐怖,以及音乐与巫风的结合等,还出现了以忠孝为本的伦理观念、阴阳五行思想、天人关系等,诸子百家有关美学上的许多重要特点,溯其根源,也大多与它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