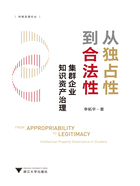
第二节 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面临的理论困境
一 独占性理论:知识资产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
法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已对知识资产治理理论作探讨,Schumpeter(1950)首次提出“独占性”一词,认为应该赋予企业对知识资产创新一定程度的专有属性,也即垄断权力,以维护创新者对获取知识资产创新投入有效回报的稳定预期。显然,创新独占性研究是Teece(1986,2006)PFI框架的具体化。
独占性体制(appropriability regime)是保障创新主体获得知识资产(创新)价值回报的外部法律规制制度安排的总和(Martinez-Piva,2009)。早期关于知识资产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考察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企业知识资产治理的影响机制。Teece(1986)首先提出独占性体制的概念,并指出独占性体制是企业知识资产治理的外部环境因素,由法律和工具性制度(legal&instruments)及技术属性(nature of technology)等外生变量决定,具有阻止知识资产(创新)被模仿的功能。随后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企业知识资产的模仿难易程度会受到知识产权法律体制和知识属性影响(Teece,2006),在特定行业或具体情境下,企业可以依托独占性体制,通过专利、版权、商标等法律手段强化企业对知识资产的专有性和垄断权,以司法权威增加知识资产模仿难度(Hurmelinna-Laukkanen和Puumalainen,2007;Samaniego,2013),而知识资产的属性,如可编码化程度也同样会影响知识资产的模仿风险,知识资产的可编码化程度(显性程度)越高,就越容易被表达、描述,也就越容易被剽窃、模仿,转移也就越容易(Teece,2006;Päällysaho和Kuusisto,2011)。但随着知识产权类型不断增多,独占性体制对于知识资产治理的失效或缺位问题也越发明显(魏江和胡胜蓉,2007):第一,法律的普适性特征要求法律规制制度安排对于所有产业的知识资产治理无差异(Mazzoleni和Nelson,2016),这就忽视了不同产业知识结构、知识隐性等知识属性差异所带来的知识资产治理方式的不同(Andersen,2004),导致传统知识产权法律的效力对不同产业也同样存在较大差异;第二,知识产权存在诉讼费用高、立案周期长、搜证难度大等问题(Fauchart和von Hippel,2008),难以有效应对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等产品特征(Levin,1986),难以保证企业对其知识资产的专有性;第三,知识产权法律的设立并不能保证所有人会遵守(Agarwal等,2009),尤其是国内大多数企业主及相关负责人的知识产权意识还相对薄弱,企业对于创新知识资产的独占性效果也就大打折扣(Martinez-Piva,2009)。
随着企业快速发展与网络情景嵌入,企业知识资产治理机制也开始由外生的环境变量逐步向内生的战略选择拓展。新涌现的知识资产治理机制,已不再局限于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依赖,而是成为企业主动开展知识资产治理的战略选择,也不再狭隘于对企业知识资产的隔离独占,而是增加了联结机制的内容,使得企业知识资产(创新成果)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共享、共创、共赢。Levin等(1986)在原有专利保护企业知识资产基础上,引入商业秘密、学习曲线等层面的内容,发现新涌现的独占性机制的有效性受到企业规模、知识性质和产业技术特性等诸多因素影响(Neuhäusler,2012)。如对于制造业的知识资产创新而言,虽然采用专利来保护知识资产的有效性要稍优于商业秘密,但是,时间领先与学习曲线仍然是制造业知识资产治理最有效的手段。Cohen等(2000)以美国制造业为对象展开分析调查(CMS调查)并得出结论:制造行业中的创新独占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一是专利,二是商业秘密,三是时间领先与互补能力(Cohen等,2000)。专利除了在一些特殊行业(如医药品、生物医疗器械以及特殊用途机器行业等)作为企业知识资产治理的有效手段被广泛应用之外,在其他绝大多数行业中的使用情况欠佳,而商业秘密和时间领先则几乎在所有行业中都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知识资产治理手段(Päällysaho和Kuusisto,2011;Neuhäusler,2012)。Hurmelinna和Puumalainen(2007)以299家芬兰企业为研究对象,对知识资产治理手段进行了有效性检验、策略补充和机制归纳,形成一整套较完整的企业知识资产治理框架,包括人力资源管理、知识隐性、技术手段(如数据加密、访问权限等)、知识产权制度(IPR,如专利、版权、商标等)、契约和劳动法以及时间领先(如市场进入、持续改进)等。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围绕知识资产治理展开更深入的质性探讨、定量检验、规范分析和创新调查等,系统梳理了企业知识资产治理策略,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基于是否依赖正式法律,将企业知识资产独占性机制分为正式机制(专利、版权、商标等)和非正式战略性机制(复杂设计、时间领先等)两种类型(Faria和Sofka,2008),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非正式机制分为半正式和非正式机制(Hurmelinna-Laukkanen和Puumalainen,2007;Luoma等,2011)。
集群情境下,独占性视角对企业知识资产治理问题的解释失效。传统知识资产治理逻辑是以建立创新成果(知识资产)的独占性为原则的,这种治理机制建立在“隔离机制”基础上,相关研究大多在宏观体制和微观企业层面展开,基于“个体创新”或“封闭式创新”情境,治理手段主要是利用知识资产本身的特质或属性(产品、过程、缄默性和被编码等)及制度手段(专利、商标、版权等)。而随着集群网络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发现集群内关联企业具有地理、制度、认知上的高度邻近性(Boschma,2005),加之集群内各类人员的高频流动性,使得传统独占性机制无法有效避免技术模仿、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Davis,2004)。更加严重的是,非正式集体学习的存在导致企业知识、技能的快速溢出,而溢出的知识、技能绝大部分以不可编码的知识资产形态存在,难以形成正式知识产权,进而导致企业知识资产治理问题在集群层面与微观层面有很大的不同,现有独占性理论难以解决集群企业收益独占的问题,出现独占性视角对企业知识资产治理问题的解释失效问题(魏江和胡胜蓉,2007)。
二 制度理论: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的理论基础
企业作为一种微观制度安排,在知识资产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张强(2005)和邢定银(2006)等认为,企业知识资产是企业内部关于知识要素使用权的制度安排结果,知识资产的形成受国家、社会、企业内部制度的共同影响。当知识资产在内外部制度作用下产生后,企业通过适当的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可以形成一种“隔离机制”(Rumelt,2005),确保了知识资产的专用属性,并更好地从中获利。Liebeskind(1996)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定义了企业的三种制度能力:激励相容能力(incentive alignment)将企业内各利益相关者联合起来,使大家具有共同激励,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知识交易成本;雇佣能力(employment)通过职位设计和对员工行为的规范,加强对员工的控制;重组能力(re-ordering)通过增加对员工的长期激励,减少其流动性。他同时指出,与市场机制相比,这三种制度能力能够更好地保护企业的知识资产(Liebeskind,1996)。
宏观制度环境影响企业知识资产治理和创新策略。Lu等(2008)分析了宏观制度环境对企业知识资产创新和治理的作用。一是合法性,即知识必须适应其所在的制度环境,满足制度的要求。按照Suchman(1995)对合法性的定义,组织的产出、目标、行动等都必须和制度相适应来获得合法性,所以组织的知识资产也必须被社会的规制、规范和认知所接受。二是制度依赖性。知识往往反映了企业对于制度系统(如国家、监管当局、传统信仰和社区)的运行以及制度规则设计缘由的理解。因此,在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下,企业必须根据制度因素构建、开发、维护其知识资产。三是知识创造、传播和转移的有效性和效率部分取决于制度基础。如知识产品的盗版现象在亚洲猖獗,正是因为缺乏制定和/或执行强有力的法律保护知识资产(Hill,2007)。
中观层次出现了新的制度规则和社会规范,通过合法性机制来约束组织和个人的行为(Meyer和Rowan,1977)。当法律不能有效保护产权时,有研究基于正式契约,讨论私人协议(契约)在满足产权所有者专有性、排他性需求时的作用机理(Dixit,2009),如竞业禁止协议、保密协议、不竞争协议等均成为知识产权法律规制制度安排的重要补充(Hertzfeld和Link等,2006),共同构成创新主体知识资产治理的外部制度安排;也有研究基于非正式契约,在一个系统中,通过信任关系(Bernstein,2016)、第三方(Howells,2006)、行业规范(Fauchart和von Hippel,2008)、声誉机制(Howells,2006;Provan和Kenis,2007;von Hippel,2007)等协调和管制活动,抑制成员企业占用其他成员的知识资产和创新成果等机会主义行为(Kenis和Provan,2006)。
综上,知识资产治理主体不仅是企业本身,还可以是上下游企业、联盟或社群、第三方机构等,而知识资产治理体系不仅包括正式司法制度,还包括一系列具有场域特征的正式、非正式制度安排。
三 合法性: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的微观机制
制度理论中合法性是连接组织行为和环境的桥梁(Hannan和Freeman,1989;Suddaby和Greenwood,2005)。合法性研究源于制度理论(Meyer和Rowan,1977),并由Weber(1958)首先引入组织研究,强调了组织行为、结构与制度规则之间的一致性。此后,Parsons(1960)针对合法性来源指出:合法性不应局限于驱使组织行为、结构一致于规制系统(regulation system),还应一致于所嵌入社会情境中共享或普遍的价值观、文化规范、社会信仰等(Parsons,1960)。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对合法性概念做了进一步扩展,提出社会认知(cognition)的重要性,强调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人的决策行为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依据组织行为、结构与个人价值观和社会认知的一致性,来判断组织价值和可接受程度。因此,合法性成了连接组织行为和环境的桥梁,企业嵌入制度场域内,感知外部环境预期并改变和决定企业战略行为,迫使其形态、结构或行为与场域规则、规范、社会理念或文化等保持一致(Meyer和Rowan,1977;Suchman,1995;Scott,2001;Peng等,2008;Menguc等,2010)。
合法性内涵。Parsons(1960)将合法性定义为嵌入特定场域内组织的行为与场域系统中可接受的行为准则间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合法性研究得到了资源依赖、组织文化和组织生态等理论支持,其中,Scott(1995)和Suchman(1995)的研究成为合法性理论研究发展中的里程碑。Scott(1995)认为组织合法性反映企业遵从相关法规、实现文化对齐和规范支持的一个状态,可以划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Suchman(1995)则给了组织合法性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定义,即“在某一包含标准、价值观、信仰和定义的社会建构体系中,实体行为是有意愿的、合适的或恰当的普遍性感知或假设”。以上两个界定是目前被最广泛采纳的内涵。
合法性的前因。基于制度理论这一理论渊源,资源—制度视角、文化—制度视角与生态—制度视角均为合法性前因研究提供了思路。Meyer和Rowan(1977)首先将合法性和资源进行了关联,认为两者的联系来自对组织有效性和制度权威性的遵从,组织规模、组织多元化水平等因素是合法性的前因。Meyer和Scott(1983)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对组织支持的程度给合法性带来的影响,文化作为认知层面的合法性前因,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组织的存在、运行和权限。Dacin等(2007)进一步将合法性的讨论扩大到组织生态范畴,认为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对组织生存同样重要,因而慈善捐赠、战略联盟等因素也成为合法性的重要前因。
合法性后果。基于以上理论视角,学者们对于合法性后果的研究都集中在合法性和组织绩效的关系之上。第一类观点认为合法性可以提高组织绩效。Zimmerman和Zeitz(2002)基于“资源—制度”视角,认为合法性可以促进企业资源整合,促进新创企业的组织成长。Kumar和Das(2007)基于“生态—制度”视角,认为联盟中的合法性可以促进成员间合作行为的发生,形成指导各个组织行动的联盟职责框架,降低成员组织间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成员组织的绩效与发展。第二类观点认为合法性不利于组织绩效。Oliver(1997)指出,合法性导向会引导组织基于社会正当性的规范理性做出决策,而并非基于盈利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做出决策。基于此,企业在合法性驱动之下,倾向于对合法性强的组织进行模仿,这种模仿往往不利于企业的差异化发展,甚至背离自己的资源禀赋对企业盈利产生负面影响(Barreto和Fuller,2006)。第三类观点认为合法性与组织绩效之间并不呈现线性关系。Shane和Foo(1999)提出环境维度和时间维度可能改变合法性与绩效的关系。Forstenlechner和Mellahi(2011)认为适度的战略相似性与绩效是正相关的,挑战了传统制度理论中认为的组织间相对同质性对组织绩效的正向作用。
合法性获取机制。传统制度理论认为,组织可以通过适应和遵从来自管制机构的强制压力、来自专业化过程的规范压力、来自不确定环境的模仿压力,采纳与制度场域相容的组织行为与结构特征,获得合法性(Powell和Dimaggio,1983);不同于遵从合法性研究中相对被动的思路,有学者基于战略视角,认为合法性是一种重要资源,可以通过操控相关群体受众的社会认知,帮助企业组织获取合法性,因此,有学者提出遵从、选择和操控三种策略(Suchman,1995)。Zimmerman和Zeitz(2002)基于此,进一步提出企业组织可以通过主动创造新的制度情境,如规则、标准、价值、信仰和模式等,以使自身行为或组织结构与新创制度情境要求相一致,从而获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遵从、选择、操控和创造共同构成企业获取组织合法性的重要机制。
合法性压力被理解为企业感知外部环境预期并改变和决定企业战略行为,促使企业形态、结构或行为变得合理、可接受和易获得支持的规则、规范、社会理念或文化的作用力(Meyer和Rowan,1977;Suchman,1995;Scott,2001;Yiu和Makino,2002;Peng和Wang等,2008;Menguc和Auh等,2010),其来源既包括相关利益者,如监管机构、专业组织、顾客、同行企业等,也涉及更为宽泛、更为抽象、难以明确压力来源的市场和非市场因素,如势力、模板、脚本、文化框架、社会事实和共享意义系统等(Greenwood和Hinings,1996;Delmas和Toffel,2008)。内嵌于特定制度场域,企业行为并非总是追求短期收益的“效率型驱动”,必然会受到合法性压力的塑造和影响(Kostova和Zaheer,1999),企业行为只有与场域规则、规范、社会理念或文化等保持一致,才能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才能获取合法性,才能在制度场域内生存,进而实现自身可持续、健康发展(Meyer和Rowan,1977;Delgado-Ceballos和Aragón-Correa等,2012;Berrone和Fosfuri等,2013)。合法性压力通常被分为三类(Powell和Dimaggio,1983;Teo和Wei等,2003;Liu和Ke等,2010;Boutinot和Mangematin,2013;Cao和Li等,2014;Li和Zheng等,2017):强制压力是企业感知到的组织外源性提供者(exogenous providers)或具有权威、强制力的重要机构(如风险投资家、银行或政府机构)带给企业组织的一种强制力,迫使企业组织采用某种结构或行为模式,若组织不顺从或者违反这种强迫,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规范压力是企业感知到的高校、行业专家、专业咨询机构等在企业专业知识的形成及推广过程中带来的压力,迫使企业与场域集体观念或者集体的思维方式趋于相同;模仿压力是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从获得成功的同行企业的行为模式与组织架构方面感知到的压力,迫使企业为克服环境不确定性,模仿成功企业的行为实践或组织结构。
合法性研究的理论机制。Suchman(1995)指出,战略观和制度观是合法性研究的两个重要视角:一部分研究是遵循战略管理的研究传统,从组织微观视角出发,认为合法性是一种资源,可以通过有目的地选择、操控甚至创造性的制度环境,进而得到制度环境的支持,以获得相应的合法性(Dowling和Pfeffer,1975;Pfeffer,1981;Ashforth和Gibbs,1990);另一部分研究则遵循原有制度理论研究传统,这类研究一般立足于超然的立场,基于宏观视角或产业视角,强调企业感知的制度或文化对组织行为与结构所产生的压力,并不是单个组织可以操控的(Meyer和Rowan,1977;Meyer和Scott,1983;Powell和Dimaggio,1983;Zucker,1987;DiMaggio和Powell,1991)。
综上,以上两个视角有两个明显的区别。首先,处理问题态度相反。基于战略视角的学者更多地将合法性视为一种可操控的资源(Zimmerman和Zeitz,2002),能够给组织带来良好绩效和竞争优势(Dowling和Pfeffer,1975;Ashforth和Gibbs,1990;Suchman,1995);而基于传统制度视角的学者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制度及其构成要素本身,并把组织获取合法性看作理所当然,合法性高低取决于受到利益相关者支持与信赖的程度(Meyer和Rowan,1977;Meyer和Scott,1983;Powell和Dimaggio,1983)。所以,在传统制度视角下,组织获取合法性源于外部制度压力的驱动,其合法化的过程是一个被动同构的过程,而在战略视角下,组织获取合法性是源于内生的一种驱动力,其合法化过程往往是一个积极作为的过程。其次,看待问题立场不同。基于战略视角的学者是站在组织管理者的身份立场,由组织内向组织外看(looking out),试图引导、启发观众认为组织行为或者结构与社会规范、价值观和信仰相一致(Elsbach,1994;Beelitz和Merkldavies,2012);而基于传统制度视角的学者是站在旁观者的身份立场,由组织外向组织内看(looking in)(Elsbach,1994),试图通过同构,使得组织行为或结构与社会规范、价值观和信仰相匹配(Beelitz和Merkldavies,2012)。这两个视角的文献往往相互渗透且难以完全割裂开来(Suchman,1995)。在组织发展过程中,既面临着外部制度环境迫使组织同构所产生的合法性压力,也面临着企业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战略性选择,不能一味地遵从外部制度环境,也不能一味地在效率趋势下采取战略活动,而忽视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组织是选择改变自身行为或结构,以获取所处制度场域环境更大程度的支持与接收,还是改变所处制度环境,创造新的制度(Zimmerman和Zeitz,2002),取决于环境不确定性、组织目标与制度环境匹配度、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力以及法律规制的强制力等因素(Oliver,1991)。
四 制度创业: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制度的形成与演化机制
制度理论假设制度场域中的法律强制规则与社会文化规范是约束组织和个人行为的一种常识,通过“合法性”来约束组织行为(Meyer和Rowan,1977)。企业组织嵌入特定制度场域会受到来自管制机构的强制压力、专业机构的规范压力以及成功同行企业的模仿压力的影响和约束,而趋向“同构”;然而,企业在面对合法性压力时,是否可以反作用于制度本身,推动与企业行为相一致的合法性压力重构,实现合法性的获取?在Eisenstadt(1980)研究的基础上,DiMaggio(1988)提出制度创业,将行动主体的能动性纳入制度分析当中,以解决上述“嵌入能动性悖论”(the paradox of embedded agency)问题,探索面临外部制度环境倾向于保持不变的压力下,行动主体如何促进新制度产生(Holm,1995;Seo和Creed,2002)。制度创业强调,由于预见到改变现有场域制度或创造新场域制度所蕴含的潜在盈利机会,企业组织会通过主动创造、推广使其行为获得普遍支持和接受所需要的强制规则、社会规范、文化信念或行为模式等,进而获取合法性并从中创造和利用盈利机会(DiMaggio,1988;Rao等,2000;Maguire等,2004)。
早期关于制度创业的研究重点关注组织个体行为或特征对场域制度重构的能动性作用。Oliver(1991)最早对制度创业过程中的组织策略做了重要探索,在此基础上后续学者做了进一步完善,如怎样的行动者成为制度创业者(Greenwood等,2002)、制度创业涉及哪些关键要素(Maguire,2004)、哪些因素影响了制度创业活动顺利实施(Hargadon和Douglas,2001;Kostova和Roth,2002)等,其中如何通过组织战略行为能动性建构场域新制度的研究最多(Suchman,1995;Zimmerman和Zeitz,2002),如企业社会责任行为(Bowen和Newenham-Kahindi等,2010)、跨国经营行为(Gifford等,2010)、战略联盟行为(Dacin等,2007)和创业行为(Tornikoski和Newbert,2007)等。
近期制度创业研究开始关注网络层面的集体行动对场域制度重构的作用(Rao等,2000;Lounsbury和Crumley,2007;Canales,2017),强调制度创业可以是一个涉及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数量的行为主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协调或非协调方式开展活动的集体现象。Miles和Cameron(1982)在对美国烟草公司的案例分析中发现,美国六大(big six)烟草公司为了应对“反吸烟运动”给其商业行为带来的合法性丧失威胁,通过集体协调的行动方式创造新组织开展集体行动,并使之获得新的可能意义与身份(Miles和Cameron,1982),如联合组建政治战略委员会、联合雇佣说客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政府的立法实践(如抵制政府批准通过针对烟草商业活动的处罚性或禁止性法律条文)、联合组建烟草研究会来推动科研活动的开展以应对外科医生协会把吸烟与癌症联系起来的行为等;此外,制度创业也可以通过非协调性集体行动开展,这种情况下制度创业是大量拥有不同程度、不同数量、不同类型资源的行为主体能动性、发散性制度创业活动的累积(Holm,1995;Lounsbury和Crumley,2007),Dorado(2005)将这种非协调的集体行动称为“制度共担”(institutional partaking)。
从以上独占性理论和制度理论相关文献回顾来看,首先,目前关于知识资产治理的研究大多仍聚焦于独占性机制,试图从微观企业和宏观制度层面寻找知识资产治理的途径,而针对集群特征开展知识资产治理的讨论尚待深入。在基于“独占体制”和“隔离机制”的知识资产治理机制不能很好地解释产业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或者范式来解析这个难题,探索适应和推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所需要的知识资产治理机制。其次,对比合法性与独占性机制/体制的关系,可以发现,合法性与独占性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关联:独占性体制/机制是获取创新成果独占合法性的制度保障,合法性是较独占性更大的范畴,是保障企业从创新中获益的规范、规制和认知。在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过程中,基于Zimmerman和Zeitz(2002)的研究,通过遵从、选择、操纵和创造四种合法化策略,组合开展的战略行动获取组织合法性,进而“从创新中获益”。最后,目前制度理论的研究开始将目光投向场域层次,强调组织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然而过于强调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导致组织在跨越合法性门槛时的趋同现象,忽略了微观组织对推动场域合法性门槛的建构作用及其对制度本身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