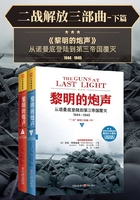
可怕的血肉磨坊
7月前,已有100万盟军士兵登上了诺曼底滩头,但双方似乎陷入了与在安齐奥类似的对峙局面,悲观点说,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堑壕战,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帐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迷宫般的战壕,其顶部覆有松树原木和沙袋。“他们不停用迫击炮轰击我们”,奥瓦尔·E.福伯斯中尉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平民永远无法想象这种生活有多残酷。”尽管已经攻下瑟堡,但在刚刚跨入7月时,滩头阵地的部分地段纵深依然只有6英里,卡昂和圣洛仍处在德国人的控制之下。
诺曼底的每日伤亡超过了1917年第三次伊普尔战役期间英军在佛兰德斯的每日伤亡数,其中还包括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帕斯尚尔争夺战中的英军伤亡。一名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将领将诺曼底地区的战斗描述为一个可怕的血肉磨坊:“11年战争岁月、两次大战,我从未见过这种情形。”奥马尔·布拉德利感叹道:“我承担不起在此处周旋的代价。我失去了手下最棒的小伙子,那些勇敢地把头伸出掩体,随后被炸飞的家伙。”
艾森豪威尔的参谋们几乎没有思考过,若“霸王行动”陷入僵局,盟军该如何是好。他们考虑过几个方案,包括在诺曼底阵地外实施另一场空降和两栖突击。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唯一可靠的解决方案便是猛攻:“集中所有可用的空中和地面力量,从已夺取地区展开一场突破。”
随着一份份伤亡名单送抵,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的紧张不安越发加剧。他已将香烟的牌子换成“切斯特菲尔德”,但每天仍要抽上好几包,这使他的血压读数略显惊悚:高压176,低压110。一名军医给他开了些降压药,这种药会导致耳鸣,不过没关系,反正他在此之前就已患上耳鸣了。他吃不好、睡不香,这是因为V-1火箭的袭击常迫使他躲入刚翻新过的防空洞,那里的油漆味熏得他头疼。7月1日,一枚飞弹在距离艾森豪威尔办公室200码处爆炸,将窗格吸出窗户,还剥落了一些屋顶。在红色皮革封面的日记本上,这位盟军最高统帅不高兴地写道:“布拉德利向南面的进攻已推迟至7月3日。真是痛苦!……试着打了打桥牌。真是糟透的一天。”
7月初视察诺曼底滩头时,艾森豪威尔住进了布拉德利的指挥所中,他总在夜间穿着红色睡裤和拖鞋来回踱步。一天下午,他挤入一架被拆掉机载电台的P-51野马战斗机的后座,向西飞行了45分钟后转向南面飞行,而后又向东飞往巴黎,对整个战场作了一番高空勘察。他承认:“若是被马歇尔知道,他肯定会怒斥我。”当被告知一名在瑟堡俘获的德国军官拒绝交代德军在哪些地段设置了地雷后,艾森豪威尔说道:“毙了这个混蛋。”这道命令并未传达下去,也未被执行。
蒙哥马利曾设想过,登陆海滩与突破敌方防线之间这段时间会有一场消耗战,他称之为“混战”。艾森豪威尔被此种设想激怒了。7月7日,在一张以“亲爱的蒙蒂”开头的便笺上,他写道:
我很熟悉你的计划,大体而言是牢牢守住左翼,并吸引敌人所有装甲部队,而右翼沿半岛推进,进而威胁与英国第二集团军对垒的敌军后方及侧翼……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以一切可能的力量防止一场僵局……我将全力支持你作出相应决定,以阻止僵局的出现。
蒙哥马利于一天后作出的回复有些虚张声势,且显得漫不经心。当天,仅加拿大第3师便有1 200人伤亡,其中330人阵亡。尽管如此,蒙哥马利仍写道:“我对情况非常满意,我已看到胜利的曙光。”随即又补充道:
我认为这场战役进展得非常顺利,敌人在所有局部战场都遭受着我们的猛烈攻击。我们已经干掉了不少德国人,所以有一点你可以肯定:这里绝不会出现僵局。
于是争执又出现了。这种直接而专业的交流中隐藏着不和谐的气息,它已感染了整个盟军最高统帅部,且愈演愈烈。蒙哥马利在日记中抱怨说:“他总在插手和多嘴,还一直大声嚷嚷!……我非常喜欢他,但永远无法与他共事,因为他不能与人平和地交流!”蒙哥马利声称,自己花了1/3的时间“确保不被解职”,1/3的时间激励部队,“剩下的1/3则用于击败敌人”。
盟军最高统帅部中,被蒙哥马利冠以“大风首脑”这个绰号的一群人强调,按计划展开的战斗引发了强烈不满情绪,特别是英国空军指挥官们。“蒙哥马利变得有些独裁,令人难以理解。”某人写道,“你很难揣测他的想法,也很难找到一个支持他的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英国皇家空军元帅阿瑟·W.特德爵士在6月下旬告诉丘吉尔,计划中的81个空军中队,能从诺曼底起飞的不到一半,因为那里只建成了13座简易机场。“问题在于蒙蒂,既不能解除他的职务,又无法让他投入行动。”特德在日记中写道。持续的降雨使得气氛又惆怅了几分,温度似乎一直在下降,愁眉苦脸的利·马洛里不由自主地拍打着便携式气压计。“事情麻烦了”他抱怨道,“搞不好会出现冰川。”
丘吉尔越来越急躁。美国人的优势日益增长,他担心英国的贡献被低估,于是要求将加拿大军队的伤亡“算入英方的伤亡人数里”,否则他们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美军伤亡人数中的一部分。这一点对凸显大英帝国的重要性而言十分关键。德军V-1火箭对伦敦的持续袭击令丘吉尔产生了残忍的想法,他开始谋划一场生化武器反击战,比如炭疽看上去就很有效;或者实施一场更为传统的战役也不错,罗列100座规模较小、防御薄弱的德国城市,宣布盟军将“一个接一个地轰炸它们,直至它们灰飞烟灭”。
这两个想法都未获得英国统帅部的青睐,主要是因其实用性不足。但丘吉尔在7月6日时仍坚持认为,须得先做“一番冷酷无情的计算”,以确定毒气战是否能缩短战争进程,同时对“十字弓行动”中确定的德军导弹发射基地实施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人都使用了毒气,卫道士们和教会从未抱怨过一个字。现在,这个话题却开始涉及道德了?荒谬!”丘吉尔争辩道。他还指出,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不轰炸城市就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但“现在每个国家都这么干。对妇女们来说,这其实就是裙子该长一些还是短一点的区别”。身处伦敦的战略家们回复说,毒气对纳粹德国“至多造成些骚扰性效果”,而且这将导致大规模化学战,伦敦也难以幸免。
艾森豪威尔在获知这场讨论后,给自己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写了一张措辞严厉的便条,暂时结束了这番争论:“我不会参与报复行动,也不会使用毒气。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集中注意力,思考些正常的问题吧。”
★★★
蒙哥马利的作战计划需要美国第一集团军发起一场猛攻,扩大桥头堡,但结果令他很失望。带着过高的希望和过少的想象力,布拉德利命令3个军于7月3日沿三条碎石路展开部队,同时发动进攻。第8军镇守盟军防线西翼,其下3个师沿一条15英里的战线向前推进,短短12天便付出了1万人的伤亡,却只在沼泽和灌木丛中前进了7英里。“蚊虫的疯狂叮咬令战士们有些昏沉。”某部队报告道。
奥马哈海滩前方,镇守美军防区左翼的第19军正设法利用橡皮艇越过岸堤陡峭的维尔河,以及与之相邻的一条运河。但他们向圣洛西面高地的推进被拥堵、友军误伤及敌方装甲部队的反击所挫败。在中央地带,第7军的表现也没好到哪里去。在一次注定要失败的行动后,柯林斯如此说道:“这绝非我想要的结果。”第一天的激战中,第83师伤亡达1 400人。其中一个团1周内损失了5名上校,诺曼底的大片土地都躺着海明威笔下的“死者”(the deads)。一名军官如此形容诺曼底地区的惨烈战事:“那种悲痛一直伴随着我。”从阅读地图到步坦协同,第一集团军的作战技能令人不敢恭维。其将领层似乎成为了薄弱环节:2个月内,布拉德利撤换了9名将军,其中包括第90步兵师的两任师长。
一名新师长将来到倒霉的第90师,尽管这位师长自己尚不知情。西西里战役期间,布拉德利曾认为泰德·罗斯福“心太软,无法指挥一个师”,但在重新考虑后,他还是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了这一任命建议。作为瑟堡的军政长官,罗斯福忙得不可开交。其间,他还帮助第4师处理自登陆日以来的5 000余名伤亡者。他写信告诉埃莉诺,登陆犹他海滩时自己率领的步兵连,损失了80%的人员,原先的6名军官中有5位伤亡。“阵亡的是我们最优秀的年轻小伙子”罗斯福告诉她,“让我们祈祷这种牺牲是值得的。”
57岁生日临近之际,他承认自己“有一种绝望的疲惫感”,在7月10日的一封家书中,他抱怨当地雨落不止,“天知道会持续多久。这始终是个问题”。但他又补充道:“我将一辆货车车厢改造成了一个房间。它是从德国人那里缴获来的……我在其中放了张桌子和一张床,车内也被漆成白色,也许我能将它当作临时的家。”一如既往,他从《天路历程》中寻得了安慰:“也许,我双脚疼痛,前路艰难,但我必须不断前行……我心灵的平静全赖于此。”
7月12日星期三,罗斯福在与柯林斯商谈后,他的儿子昆汀于晚间7点30分来到了父亲身边。昆汀是第1步兵师的一名军官。父子两人在那辆焕然一新的德国货车内共度了两个小时。“我们无所不谈”,昆汀写道,“家庭,家人,我的计划,战争。”但就在儿子离开后不到一个小时,罗斯福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冠状动脉血栓。第4步兵师师长塔比·巴顿在夜里11点30分获知了这个消息:“我走进货车时,他尚有呼吸,但已经昏迷。”几个小时后,巴顿写信给埃莉诺:“我坐在那里,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我所知的最英勇的战士、最优雅的绅士过世……但战争仍在继续,我们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小西奥多·罗斯福准将,7月12日拍摄于圣梅尔埃格利斯。几个小时后,他因为突发冠状动脉血栓而去世。第4步兵师师长认为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英勇的战士和最优秀的绅士”。
星期五,法国国庆日,一辆军用半履带车载着罗斯福的遗体驶往墓地。车辆从一座座窗台上悬挂着自制美国国旗的小屋旁驶过,一块标牌上写着“感谢我们的解放者(Merci à Nos Libérateurs)”。师里的军乐队演奏着《战争之子亲临战场》(The Son of War Goes Forth to War),随后,两名号手吹响了安息号。罗斯福那辆名为“莽骑兵”的吉普车将回到调配场等待重新分配,车上的名字已被涂去。战争仍在继续。

罗斯福准将葬礼上的护柩者,左侧队伍前方的是布拉德利和乔治·巴顿中将;右侧的是考特尼·H.霍奇斯中将和柯林斯。(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
罗斯福并不知道,他的师长委任令就放在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也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因在犹太海滩的英勇表现而获得荣誉勋章。艾森豪威尔和布拉德利倾向于将巴顿的勋章降为杰出服役十字勋章,但乔治·马歇尔一锤定音,使自己在一战时的老战友获得了更高的荣誉。一位家族朋友写信给埃莉诺:
他有着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品质。一片连绵的山脉、一行好诗句、一种高贵的行为,这一切都能在他的精神中找到回应的火焰。我相信,世上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多,而现在,又少了一个。
★★★
德国游记作家卡尔·贝德克尔曾将圣洛描述为“一处历经沧桑之地”,查理曼大帝与“精致地坐落于维尔河右岸的一片山坡上”这句话印证了这一点。尽管遭受过维京人、安茹王朝的国王们以及1574年屠杀加尔文主义变节者的天主教守旧派的洗劫,但圣洛总能浴火重生。直到1944年6月6日,盟军的飞机将这座城市炸为齑粉。登陆日第二天拂晓前,已有800名市民身亡。整整一周,轰炸机每天都会轰炸此地,进一步粉碎交通要点,以阻止敌军车队赶往滩头战场。一个个家庭被埋入废墟,一些人逃出了这座城市,原来的1.1万名居民如今只余下不到10人。
8条公路和1条铁路从圣洛延伸而出,使这座城市成为第一集团军作战区域内最重要的地带,也是长达50英里的战线上对抗最为激烈的地段。一名记者记录道:“炮火和‘大个头炸弹’将四周的山丘炸成了一条被虫蛀过的白色毯子。”硝烟覆盖着碎石嶙峋的地面,令一名陆军观测员想起一幅以美国内战为题材的木刻版画。一个多星期来,美国士兵们每天挣扎着向前推进500码,穿过支离破碎的苹果园,跨过焦黑的山脊线,驻守在此的是身着灰色连体作战服的德国伞兵。布拉德利曾于7月11日断言,德国守军已是“强弩之末”。跨越10英里长的区域以发起致命一击的命令已经下达,奥马哈海滩的英雄——第29步兵师将直扑圣洛。率领他们的是顽固好斗的小查尔斯·亨特·格哈特少将。
“他的一切都很火暴,讲话、动作和脾气”,一名少校写道,“他是‘死气沉沉’的反义词。”作为柯林斯和李奇微在西点军校的同学,格哈特因自己的骑行风格而被此两人称作“松开的缰绳”,又因他吹毛求疵的性格而被称为“琐事将军”。
在他麾下,就连高级军官也得参加训练,以便能回答他提出的5个问题,其中之一是“描述一个人从溺水状态复苏的过程”。在美国担任师长时,格哈特曾要求所有士兵每日暴晒以获得黝黑的身躯;他还悬赏10先令,奖励那些枪法比他准的小伙子。一名下属将他描述为“顽强、严格、好斗已渗入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另一个人则认为他“完全步入歧途,应该当一名印第安人战士”。他曾喊出振奋人心的口号,“29师,我们上!”但就连他的崇拜者后来也开玩笑说,格哈特真应该指挥1个军,下辖3个师:一个师在战场上,另一个师在医院中,还有一个师在墓地里。
7月15日下午稍晚,从北面和东面发动进攻后,第29师的先头部队已逼至距圣洛不到2英里的位置。各火力小组蜿蜒穿过灌木丛,各处战场上,步兵班与挂着一挡的谢尔曼坦克齐头并进,并以之作为推进时的隐蔽物。工兵们随后用TNT和硝酸铵在树篱上炸开缺口,步兵们快步突入,但突然间,德军防线爆发出密集的火力,将美军部队掀翻在地。“整支部队就像被一根绳子猛地向后拽去。”一名军官写道。但美军回敬的炮火将德军伞兵炸成一堆“难以拼凑成一个完整人体”的碎肉。曳光弹如炽热的长针钻入灌木丛,炮火的轰鸣声撕扯着士兵的耳膜。“它听上去像是一切的终结”,一名一等兵写道,“炮火下,来到这里之前的记忆荡然无存。”在前线待了3天的士兵现在已算得上是一名老兵了。
7月17日星期一的拂晓前,格哈特命令全部9个营发起进攻。第116步兵团第3营实力已不足巅峰期的一半,勉强可达到400人,但即便如此,它仍是9个营中最强的一个。第3营以连队为单位,穿过浓雾,悄悄来到圣洛东面1英里处的拉马德莱娜镇。上午8点刚过,德国人的迫击炮弹呼啸而至,新上任的营长托马斯·D.豪伊和他的两名通讯员当场阵亡。幸得美军的炮火和P-47雷电战斗机的轮番轰炸,才使该营未被敌装甲部队碾碎。士兵们用汗衫和黄色烟雾标示出前线,然后在树篱中搜寻着派珀轻型飞机投下的血浆袋。补充兵员身穿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快步奔上前去。他们手中的步枪上,军需标签仍在扳机护圈上飘动。“这真是难以言说的场景,令人内心酸涩。”一名年轻的军官后来回忆道。
德军的防线逐渐溃散。“荷兰人”诺曼·科塔将军,这位自奥马哈海滩淬炼出的硬汉率领着一支特遣队,于7月18日下午6点从东北方进入圣洛。他们占领了一片墓地,布兰切特家族的地下墓室成为了临时指挥所。墓室的墙壁由18英寸的大理石构成,一具石棺非常适合充当地图桌。“这片死者安息之所”,唐·怀特黑德写道,“是整个圣洛最安全的地方。”在灌木丛中苦战了数周后,美军士兵终于攻入城区,聚集在巴约街。“就像一群幽闭恐惧症患者从迷宫中脱困而出般快乐。”A.J.利布林补充道。德军的炮火仍从南面高地袭来,科塔的胳膊被弹片击中,鲜血顺着他的手指流下。但美军士兵很快便控制了17个据点。按照格哈特的命令,豪伊的遗体在黄昏时由一辆吉普车送至,其身覆盖着国旗。士兵们将他放在一片碎石堆上,此处曾是圣克鲁瓦的修道院。
圣洛城内,道路几近全毁。“你无法辨别出任何东西”,诗人让·福兰写道,“无论何等坚固的物件都未能幸免。”记者艾利斯·卡彭特报道说,石屋的碎块与漆过的百叶窗将维尔河堵得死死的。“河上漂浮着地板的木块、屋顶的木料、家具、床垫……以及各种各样的动物死尸,死马、死牛、死猫和死狗。一切都是灰暗的”,一名美军士兵补充道,“即便这里被解放,也无法恢复生机了。”作为一名红十字会志愿者来到此处的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估计,2 000~2 600座建筑被“彻底摧毁”,即便在所有废墟中,圣洛也称得上是“首都”了。
军方的一份“可能设有诡雷的物件”的名单中包括:篱笆桩、茶杯、门铃、大号折刀、钱包、抽屉、电灯开关、汽车起动机、窗帘和墨水瓶。这份名单还应添加上最隐蔽的诡雷藏匿处——德军士兵的尸体。他们身上可作为战利品的鲁格手枪或钢笔通常连接着一枚手榴弹的拉弦。’美军士兵得到通知,“在战场上收拾敌方尸体时,至少得用一根200英尺长的绳子猛拽一次。”
圣洛的光复结束了布拉德利于7月中旬发起的攻势。总的说来,这是一场令人失望的战役:付出4万人伤亡的代价后,12个师向前推进了3~7英里。“如果说这片错综复杂的灌木篱墙外还有另一个世界的话”,一名幸存者写道,“你也不敢保证自己能活着见到它。”就像一名营长指出的那样,许多人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德军将采取更具毁灭性的举措”。
但圣洛之战并非一场毫无意义的胜利。用蒙哥马利的话来说,此番攻势“耗尽了德军防御的勇气”,令隆美尔丧失了维持部队东西两向机动性的重要交通网。美军在德军第9伞兵团一名阵亡士兵的身上发现了一封未完成的信,信中描述他的战友们嚼着烟叶,惊恐地紧贴着地面时的情形:“我们只觉得这个世界即将灭亡。”
在拉康布一片绿色的草地上,格哈特带领着幸存的将士们高唱《更近我主》(Nearer, My God, to Thee)时,全师近2 000名阵亡将士被安葬在白色的木十字架和大卫之星(犹太人标记,两个正三角形重叠成的六角星。——译者注)下。一位副官念着每一名阵亡者的名字,每个名字都由其幸存的战友代为回答:“到!”当师里的军乐队奏起《啤酒桶波尔卡》(Beer Barrel Polka)时,全师将士一齐高喊口号:“29师,我们上!”随后,他们再次返回战场。
★★★
7月17日星期一,与往常一样,隆美尔起得很早。为防备盟军轰炸机的空袭,他现在常与自己的参谋人员睡在拉罗舍居伊翁后方一间嵌入白垩崖的房间里,屋内镶有木条。一条名叫埃尔博的腊肠犬在行李架下打着瞌睡,隆美尔曾告诉露西,一条好狗“能让你的思绪从烦恼中挣脱出来”。在住处匆匆吃罢早餐,他噔噔噔走下15级石阶来到院中,钻入一辆霍希车的前座。他的副官、一名中士和另一位军官坐在后排,他们凝望着天空,用肉眼搜寻着可能出现的敌方战斗机。这辆大型敞篷车驶出院门,向西驶过吉维尼小镇,克劳德·莫奈曾于一个平静的时代在此处画出那幅《睡莲》。
这位德国陆军元帅打算前往法莱斯视察两个师,然后再到卡昂附近造访麾下的两个军部。他的烦恼,不是一条好狗或前一晚聆听的勃拉姆斯广播音乐会所能排遣的。对一位经常驱车200多英里去看望战地指挥官的陆军元帅来说,离开拉罗舍居伊翁并非一场小冒险,而是极度危险的旅程。德军的车队或单独行车,只能在仲夏时节夜幕垂临的短暂时间里行驶。从诺曼底到荷兰,道路两侧每隔60码便会出现一条沟壕,司机和乘客可以跳入其中,以躲避对地扫射的飞机。
“形势一点也不乐观”,隆美尔曾写信告诉露西,“我们必须为更严峻的考验做好准备。”英方飞机在40分钟内投下3 000吨炸弹,卡昂最终于7月9日陷落,但城市已然灰飞烟灭。“这里已没什么东西了”,一名目击者报告道,“只余尘埃。”8 000法国难民挤在公立中学和散发着臭气的男子修道院内。这座修道院是征服者威廉因娶了自己的表妹玛蒂尔达,为赎罪而建造的。德军依然控制着卡昂南郊,但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残余步兵实力只相当于一个营。这支屠戮之师惨遭屠戮,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
现在,B集团军群一天遭受的损失便与隆美尔的非洲远征军于1942年整个夏季的损失持平。过去6周里,德军在诺曼底地区的伤亡数已达10万,但运抵的补充兵仅有1万人。7月10日,英军对卡昂的一次炮袭共发射了8万枚炮弹,德军倾其所有,也只还击了4 500枚。隆美尔曾亲眼目睹了一位营长骑马赶回司令部索要一辆汽车和一些燃料,他在战斗日志中写道:“这些师的储备已被耗尽。”柏林方面预计,6—10月,德军在所有战线上的伤亡将达160万,远超国家的承受力。
苏军发起的夏季攻势令德军雪上加霜。6月22日,近200万红军士兵、2 700辆坦克、2.4万门大炮被投入了对德进攻中。不到2周时间,一次巨大的钳形攻势歼灭了25个德军师,在前线撕开了一个宽达25英里的缺口。就在该周星期一,数万名德军战俘将排着蜿蜒的队列徒步走过莫斯科街头。
隆美尔的不满日益加剧。他对自己的密友、海军中将弗雷德里希·奥斯卡·鲁格说:“希特勒毫不考虑德国人民,会继续打下去,直到整个德国连一座伫立的房屋也不剩为止。”陆军元帅知道这是一次危险的交谈,是关于西线的私下意见,甚至可能转化为一次政变:隆美尔反对让希特勒以死谢天下,但会考虑在必要的时候接掌德国武装力量指挥权。7月初,龙德施泰特被解除了西线总司令的职务,表面原因是其年龄和健康方面的问题,实际是因他曾建议柏林“设法结束整个战争”。希特勒为他颁发了一枚勋章并拨发25万马克养老金,令他前往巴德特尔茨疗养。隆美尔预感到自己将是下一个。
龙德施泰特的继任者是君特·冯·克鲁格元帅。克鲁格绰号“聪明的汉斯”,他曾于东线指挥一个集团军群长达2年。如今,带着“无畏、顽强的创新者”的美誉,克鲁格来到了法国。在拉罗舍居伊翁的第一次会面,克鲁格指责了“顽固任性”的隆美尔,但不到一个星期,他便承认“形势已严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7月15日,隆美尔给最高统帅部写了一份3页纸的报告,他在其中写道:“诺曼底前线局势日益恶化,即将爆发一场重大危机。这场不平等的战斗已临近尾声。”克鲁格在写给柏林的一封附信中,对这一评估表示赞同。
星期一午后,在卡昂东南方20英里处的迪沃河畔圣皮埃尔,隆美尔的霍希车驶入了党卫军第1装甲军司令部的伪装网内,炒鸡蛋和白兰地正等着这位陆军元帅享用。当日行程中,他没见到任何能缓解郁闷情绪的事物,更遑论那辆遭到扫射后在路边燃烧的德军卡车,着实让人心生绝望。在党卫军第12装甲师师长库尔特·迈尔请求获得德国空军的支援时,隆美尔沮丧而严厉地说道:“你以为自己在跟谁说话?你认为我是闭眼开车穿过这个国家的吗?”
在圣皮埃尔与约瑟夫·迪特里希将军(这位装甲军军长一度是屠夫的学徒和混迹于酒馆的斗殴者)的会谈过程中,隆美尔提醒道,一场“大规模进攻”最早可能在当晚就来临。实际上,尽管英国人试图用炮击掩饰,但已经可以看见、听见他们的装甲和架桥设备正集结在奥恩河河谷。隆美尔建议,将反坦克防御分散于10英里的纵深内,从而钝化对方的攻击,并防止盟军桥头堡与仍有可能从加来海峡发起进攻的第二股盟军力量会合。
一场大战似乎迫在眉睫,迪特里希对此表示同意:卡昂平原下的石灰岩就像一块回声板,将敌方的坦克声放大后传给任何一个把耳朵贴在地面上的人。“元帅大人”,他用带着鼻音的巴伐利亚方言说道,“我只服从你的命令,无论你打算做什么。”
下午4点刚过,隆美尔回到霍希车内,将一幅地图摊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一则坏消息需要他立即返回拉罗舍居伊翁。“我已争取到迪特里希的支持。”他低声对副官说道。
汽车沿着D-4公路向东高速驶去,脱帽的农夫和飘扬着白旗的牛车在窗外划过。在利瓦罗郊外,司机绕道驶上一条乡村小路,随后在维穆蒂耶尔重新汇入大路。北面的地平线处,6架敌军战机如蜻蜓般轻掠袭来。
突然,坐在后排的中士叫了起来,两架喷火式战斗机发现了这辆霍希,正从后方迅速逼近,机身已压低至树梢上方。司机将油门踩到底,霍希几乎就要挤入白杨树后方一条狭窄的车道,此时,500码外的领头战机机翼下射出了第一串炮弹。炮弹击中霍希的左侧,司机的肩膀和胳膊受到重创。汽车急速倾斜,撞上一段树桩后跌入一条沟渠中。隆美尔先是撞在挡风玻璃上,随后又被甩至车外,倒在距霍希车残骸20码的路面上。
他身负重伤,双耳出血、颅骨骨裂,左太阳穴有两处破裂,颧骨破碎,左眼伤得厉害,脸部和头皮也被撕裂。他随后被抬至附近一座看门人小屋,人们用了45分钟找到另一辆汽车后,将他送往利瓦罗。当地药剂师正在镇广场的咖啡馆里喝着苹果白兰地,却被急召去为重伤的陆军元帅包扎伤口。在给休克的隆美尔进行注射后,这位药剂师宣布伤者复苏希望渺茫。昏迷不醒的隆美尔被送上另一辆指挥车,来到25英里外位于贝尔奈的一所空军医院。
最终,他活了下来,在医院的9号病房内慢慢康复,直至伤势稳定到能让他返回住在黑尔林根的露西身边。没过几周,纳粹德国的宣传人员称,隆美尔在一起车祸中负伤,话中省略了敌方战斗机所发挥的作用。对埃尔温·隆美尔元帅来说,战争结束了。
★★★
隆美尔对盟军即将发起进攻的判断是正确的。7月18日星期二,清晨5点,伴随黎明的晴空光芒乍现,1 000架“兰开斯特”轰炸机从3 000英尺高空掠过波光粼粼的海峡,4 500架飞机中的第一波次将在卡昂东南方炸开一条狭窄的通道。“红色的黎明中,飞机越过海面,分散成一个巨大的扇形”,在一架小型飞机的驾驶舱内查看了一番后,利·马洛里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很快,除了硝烟和尘埃,便什么也看不见了。”一名德军坦克组员回忆道:“我看见飞机上落下许多黑点,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萌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那也许是传单吧?但随后的几个小时,我经历了一生中最可怕的事。”
单是第一轰炸波次便投下了6 000吨炸弹。一些既定目标周围的土地,平均每平方码落下了25磅高爆炸药,一名身处其中的上尉称之为“一片密集的噪声”,德军士兵即便侥幸活了下来,也因此彻底失聪。“小黑点”不停落下,起火的飞机也随之坠落,但最终,整个编队带着“坚定不移的尊严”返航了。上午7点45分,震天的高呼回荡在盟军沿奥恩河集结的装甲部队中:“前进!”二战中,由英国人发起的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开始了。
“古德伍德行动”集结了3个英国和加拿大军,约7.6万名士兵和1 370辆坦克,这柄向南突刺的匕首将插入拥有230辆坦克、600门火炮及重型迫击炮的5个德军师中。强硬的英国第8军麾下3个装甲师的700辆坦克将引领这场进攻。蒙哥马利的坦克数量充裕,但步兵数量不断减少,他告诉属下,他打算“将敌军主力吸引至东翼的战斗中。如此一来,西翼的战事进展也许能轻松些”。
计划很明确:以英国第二集团军缠住隆美尔,以便美国第一集团军能冲出滩头阵地。但这个谦逊、可靠的作战计划却受到困扰,面对掘壕据守的反坦克防御,缺乏步兵掩护使得坦克处境极其危险。蒙哥马利还告诉第二集团军司令迈尔斯·登普西:“在战斗中打击敌方装甲部队,将其削弱至对德国人再无价值的地步。”也就是说:消耗敌人,直至其毁灭。英军装甲先头部队“应向南推进至距卡昂20英里处的法莱斯”,使敌人“惊慌、沮丧”。蒙哥马利向身处伦敦的布鲁克元帅作出预言:“一场真正的决战将发生在东翼。700辆坦克散布在卡昂东南方,装甲车一鼓作气冲在最前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战地记者们相信,一场“苏联式”突破将使第二集团军向前推进100英里或更远,甚至逼近巴黎。
蒙哥马利已矫枉过正。许多人都期盼着一场可以乘胜追击并有利于盟军的大战。艾森豪威尔从蒙哥马利处获知“整个东翼将陷入一片火海”后,作出了承诺:美军将继续“奋勇作战,一刻不停,为英军装甲部队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这位盟军最高统帅在一封电报中补充道:“我以最为乐观和热情的心态看待这场战役的前景。如果你此番胜利使过往的经典之战看上去像是小规模冲突,我也丝毫不会感到惊异。请原谅我如此振奋,但这着实令人激动。”
为从态度审慎的空军指挥官那里骗取4 000架次飞机,蒙哥马利认为自己不得不“粉饰这场战斗,强调甚至过分夸大所获得的成果”。登普西在战争结束后说道:“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未向艾森豪威尔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英国情报主管威廉斯准将补充说:“蒙哥马利不得不始终保持着自负,以使人们愿意付出代价。”
前进!无论愿意与否,坦克队伍“像一支起锚的舰队”般隆隆向前,驶出了标以白色胶带的雷区缺口。为首的是第11装甲师,装甲部队近卫和第7装甲师紧随在后。奥恩河上的三座桥梁每隔20秒便有一辆战车通过,这种精心安排的声响规律很快使气氛紧张起来。他们驶过燃烧着的、齐胸高的麦地,来到一片隐蔽地带。这里果树林立,堆砌而成的石屋组成座座村落,路面向南倾斜,即使相隔甚远,也能很快发现隐蔽的敌人。“760门火炮怒吼起来,炮弹呼啸着掠过天空,就像愤怒的女人们从房间里一齐冲出来。”一名上尉这样写道。
滚动的炮弹以每分钟150码的速度向前席卷,一名坦克组成员将此描述为“一堵灰色的弹幕铁壁。很难相信有任何事物能在这种炮击中保持完整”。但弹幕越过坦克中队后不久,便在距离进攻发起线2英里处的一道铁路路基前放缓了。惊慌的德国人并未像蒙哥马利期望的那样,被一场世界末日般的进攻搞得神经错乱,他们很快恢复了清醒。
炽热、橙色的侧射火力由卡尼射出,这座饱受摧残的村庄位于进攻通道的左侧边缘。上午10点,汉斯·冯·卢克中校仍穿着他的军礼服,这位隆美尔的助手刚刚结束了在巴黎的3天休假。卢克在村里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空军炮兵连,拥有4门88毫米高射炮。卢克挥舞着手枪,强迫不太情愿的炮兵连连长将炮管瞄准一片苹果园。“你要做的就是打坦克!”一发发炮弹开始“像鱼雷般”穿过麦秸秆。英军第11装甲师报告说,“很难判断炮火的来向。”没过多久,16辆谢尔曼坦克停在麦地里起火燃烧。德军坚守卡尼村直至傍晚,妨碍了英军前进的脚步。
更多的坦克很快在南面燃烧起来,它们在越过第二条铁路路基后遭到阻击,这条路基正对着敌军沿布尔盖比岭设下的主火炮防线,布尔盖比(Bourguébus)不可避免地被英军士兵戏称为“Buggersbus”:载满同性恋的大巴车。虽然遭受了地毯式轰炸,但山脊和党卫军援兵几乎毫发无损,战斗轰炸机飞行员发现,伪装过的火炮掩体使用了无烟、无闪烁的火药,难以被发现。英军侦察队缓慢前进时,德国守军便趴下身子,“结果,侦察车发回的报告中错误地声称,布尔盖比岭没有敌人”,第11装甲师师长后来解释道。“猛烈、难以逾越的火力”随后便席卷了坦克编队。很快,“视野中满是起火燃烧的‘谢尔曼’坦克”,冷溪近卫团的一名中尉回忆道。
“一些坦克组成员身上起了火,在地上翻滚着,试图将衣服上的火苗扑灭。”炮手约翰·M.索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此刻,我们前方所有坦克都在燃烧……巨大的烟圈从炮塔腾起,直直升入无风的高空。”另一名英国士兵写道:“烧伤的战友不断穿过谷地返回。我们给了他们些水喝,告诉他们继续走。”一名下士将烧焦的布尔盖比山坡形容为“一片可怕的墓地,埋葬的是燃烧的坦克”。

1944年7月18—20日,“古德伍德行动”
11th Armored Div. 第11装甲师(英)
12SS Pz 党卫军第12装甲师
7th Armored Div. 第7装甲师(英)
BRADLEY 1st Army 布拉德利第一集团军
CHOLTITZ 84th Corps 肖尔蒂茨第84军
CORLETT XIX Corps 科利特第19军
CROCER I CORPS 克罗克第1军
DEMPSEY 2nd Army 登普西第二集团军
DIETRICH I SS Panzer Corps 迪特里希党卫军第1装甲师
GEROW V Corps 杰罗第5军
Guards Armored Div. 禁卫装甲师(英)
HAUSSER 7th Army 豪塞尔第七集团军
MEINDL 2nd Parachute Corps 迈因德尔第2伞兵军
MIDDLETON VIII Corps 米德尔顿第8军
O’CONOR VILL Corps 奥康纳第8军
SIMONDS 2nd Canadian Corps 西蒙兹加拿大第2军
Allied advance 28-31, July 7月28—31日盟军的推进
Allied Front, eve., 27 July 7月27日夜间的盟军防线
Front, eve.24, July 7月24日夜间的战线
Front, July18, Morn. 7月18日清晨的战线
Front, July20, Eve. 7月20日夜间的战线
German Front, eve., 27 July 7月27日夜间的德军防线
SATURATION BOMBING AREA 饱和轰炸区
To Falaise 通往法莱斯
BELG. 比利时
BRITAIN 大不列颠
FRANCE 法国
Argentan 阿尔让唐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Aure R. 欧尔河
Authie 奥蒂耶
Avranches 阿夫朗什
Ay R. 艾河
Bay of the Seine 塞纳湾
Benounille 贝努维尔
BOURGUEBUS RIDGE 布尔盖比岭
Bras 布拉斯
Brecey 布雷塞
BRITTANY 布列塔尼
Caen Canal 卡昂运河
Caen 卡昂
Cagny 卡尼
Cherbourg 瑟堡
Colombelles 科隆贝莱
Cormelles 科尔默莱
Coutances 库唐塞
Douve R. 杜沃河
Douvres 杜夫尔
English Channel 英吉利海峡
Falaise 法莱斯
Faubourg de Vaucelles 沃瑟莱近郊
FORET DE CERISY 瑟里西森林
Frenouville 弗雷努维尔
Giberville 吉贝尔维尔
Granvile 格兰维尔
Hubert Folie 于贝尔福利耶
Isigny 伊西尼
JUNO 朱诺滩
Laize R. 莱兹河
Le Havre 勒阿弗尔
Le Mans 勒芒
Lessay 莱赛
Lion-sur-Mer 滨海利翁
London 伦敦
Mathieu 马休
Mont.St.-Michel 圣米歇尔山
Mortain 莫尔坦
NORMANDY 诺曼底
Odon R. 奥东河
Orne R. 奥恩河
Ouistreham 乌伊斯特雷昂
Percy 珀西
Periers 佩里耶
Petit Enfer 小地狱
Pontaubault 蓬托博尔
Pont-Hebert 蓬埃贝尔
Quiberon 屈伊伯克
Ranville 朗维尔
See R. 塞河
Seine R. 塞纳河
Selune R. 塞吕讷河
Seues R. 瑟斯河
Soulle R. 圣苏尔河
Sourdeval 苏尔德瓦
St.-Aubin-Arquenay 圣奥班达尔屈埃奈
St.-Aubin-sur-Mer 滨海圣奥班
St.Gilles 圣吉莱
St.-Jean-de-Daye 圣让德代埃
St.-Lo 圣洛
St.-Malo 圣马洛
St.-Martin-de-Fontenay 圣马丹德丰特奈
St.-Nazaire 圣纳泽尔
STEEL WORKS 钢铁厂
SWORD 剑滩
Torigny 托里尼
Touffreville 图夫雷维尔
Troarn 特罗阿尔恩
Villedieu 维莱迪厄
Vimont 韦芒
Vire R. 维尔河
Vouilly 武伊利
★★★
蒙哥马利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今天早上的行动圆满成功”,下午4点刚过,他给布鲁克元帅发去电报,“局面大有希望,很难想象敌人现在还能做些什么。”在发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他补充道:“我对今天发生在东翼的战斗非常满意。我们肯定令敌人毫无准备。第二集团军的3个装甲师目前正在旷野奋战。”但这纯属他的主观臆想:第8军沿一条并不比刀刃宽多少的前线勉强向前推进了6英里,付出的代价是200辆坦克。也许是被先前从战场发回的急电中愉悦的情绪所误导,他还签发了一份公告,及时赶上了BBC晚上9点的新闻广播:“第二集团军发起进攻并达成突破。蒙哥马利将军对此非常满意。”7月19日星期三早晨,《伦敦时报》的头版头条上写道:第二集团军达成突破。不甘示弱的《每日邮报》则刊登出标题:装甲部队现已涌入敞开的国家。
蒙哥马利振奋人心的宣言在布希公园引发了欢呼,可当真实的作战态势图明确后,这种欢呼变为了巨大的失望。星期三,凯·萨默斯比在她的工作日记中写道:“E担心不已,因为蒙蒂停步不前。艾森豪威尔感觉不舒服,血压升高。”(E指艾森豪威尔。——译者注)当天的事情只会令E感觉更加糟糕。据报,布尔盖比岭上“满是敌人”,包括已令更多谢尔曼坦克在卡昂平原上起火燃烧的反坦克援兵。登普西用于实施侧翼进攻的两个军——东面的英国第1军和西面的加拿大第2军,也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功。
前者在特罗阿恩发起的多次进攻均告失败;后者虽然夺取了卡昂南郊,却又在德军的一次凶猛反击中被击退。据一名加拿大士兵记录:“有一个被困的旅,幸存者们躲在麦地里,直到他们匍匐行进至安全处为止。”星期四拂晓时,英国士兵终于攻占了布尔盖比岭,但没有继续前进。下午4点,一场雷雨“带着热带暴雨的劲头”降临,长达两日的倾盆大雨结束了“古德伍德行动”。军士们分发着朗姆酒,士兵们蹑手蹑脚地穿过战场,搜寻着阵亡的战友。
这场攻势又解放了34平方英里的法国领土,以及卡昂的其余部分。这将滩头阵地扩大至足以容纳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先头部队的程度,但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期望仍然有一定差距。2 000多名德军士兵被俘,此外,正如蒙哥马利预想的那样,德军额外的装甲力量被吸引至盟军东翼。但约瑟夫·迪特里希只损失了75辆坦克和突击炮,并未像蒙哥马利所希望的那样大伤元气。所谓的“装甲师拼死突击”仅仅使第二集团军付出了4 000多人的伤亡,外加400多辆坦克,这个数字约为英军部署于欧洲大陆的装甲力量的1/3。空军力量则一直为“7英里的范围内投下了7 000吨炸弹”而抱怨不已。
耗时近7周后,“霸王行动”已在一条80英里长的战线上投入了33个盟军师,但对诺曼底的纵深突破还不到30英里,却付出了12.2万人伤亡的代价。“我们面对的问题,比最悲观的人在战斗开始前所设想的更为艰辛。”艾森豪威尔的密友埃弗雷特·S.休斯少将于7月22日写信告诉他的妻子。机智的家伙写出了嘲弄性的报纸头条——“蒙哥马利端坐于他的卡昂”,而《纽约先驱论坛报》则捕捉到了前线的沮丧情绪:“盟军在法国的整条战线陷入了困境。”《伦敦时报》一改对“古德伍德行动”的热情:“先前报道中所用的‘突破’这个词,其含义是有限的。”利·马洛里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的问题在于某些将领的指挥能力不足。”
盟军统帅部里的抱怨和指责愈演愈烈。蒙哥马利会被解除职务吗?谣言四起,鼓动者们煽风点火。获知V-1发射场不会被迅速攻占后,空军上将特德告诉比德尔·史密斯:“那么,我们必须换个能把我们带至那里的将领。我、艾森豪威尔,还有其他人一直都被当成了傻瓜。”更严重的是,特德告诉艾森豪威尔:“我认为蒙哥马利从未想过要达成一场干净利落的突破。”这番话是他于7月20日,德国军方企图用一枚炸弹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所说。双方依旧在诺曼底战场僵持着,希特勒因此得以腾出手来实施报复,并稳固自己的政权。失败的暗杀者,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和其他200多人被枪毙、绞首、斩首、服毒或吊死,有些还被拍成了影片,另有数千人被捕入狱。
到了当月月底,德国国防军军官被要求使用纳粹举手礼,而不是传统的军礼,以此展示其对元首的忠诚。“E对所取得的进展很不高兴。”萨默斯比写道。尽管不太高兴,但他还是定下心神,决定不轻举妄动,只是静观其变。相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他继续给手下的战地指挥官施加压力。一天晚上,在被丘吉尔打来的电话吵醒后,艾森豪威尔问这位英国首相:“你的国民如何看待此地缓慢的进展?也许你能说服蒙蒂跨上他的自行车动起来。”
至于蒙哥马利,盟军最高统帅向他发送了一份14段长、措辞清晰的电文。“时间至关重要”,艾森豪威尔写道,“我们必须投入一切力量展开攻击。我想,我们最后会逮住他们,并消灭他们,但这一时刻尚未来临。最终,美国的地面力量必定远超英国,但在我们实力相当时,我们必须并肩前进,共享荣誉、分担牺牲。”
他将继续保持信心,对作战计划、对他的各级指挥官,以及他们共同的事业。也许他只会对自己的母亲透露出自己是多么疲惫。7月23日,他在寄给居住于堪萨斯的艾达·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写道:“若是能回家,我就躺在门前的草坪上,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待上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