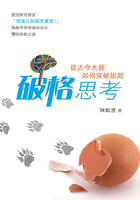
物種起源學說的線索
達爾文(C. Darwin)的“物種起源”學說,源自三個本來互不相關,但本身已是比較完整的線索,它們在某些特殊條件下,驀然契合─其過程也是如柯斯勒(A. Koestler)所說的達成創造性行動的“偶聯作用”。
第一條線索是進化論:根據達爾文晚年寫的自傳,他是在1836年,作為博物學家隨“獵兔犬號”戰艦考察南美洲後,成為進化論者的。在那次旅途中,他深深感受到繁殖於那個大陸的有機生物的分佈特點,尤其是那大片土地的地質地貌,與今日及往昔聚居於此的種種生物之間的關係。這些都給予他提示,說明現存物種早經過千萬年的演化,並非從盤古初開就是這個樣子。這個想法一點也不新,在1794~1795年間,在德國的歌德(J. Goethe)、英國的伊拉斯謨斯•達爾文(E. Darwin,查理斯•達爾文的祖父)、法國的聖•希耶爾(G. St. Hilaire)已鄭重提出此觀念,那時距達爾文的出生還要早15年。
第二條線索是演化的機制:那就是說,物種是怎樣變異的呢?當時進化論者裏的主流學派,以拉馬克(J. B. Lamarck)為代表。他認為,動物的軀體特徵都由“需要”所決定,特殊的器官會根據它是否有實際用途而長出或萎退,而且這些在動物生命過程中產生的變化,還會遺傳給下一代。換句話說,長頸鹿的脖子長就是因為要吃樹上的葉子,而長脖子又可以通過遺傳,成為子子孫孫的特性。
但達爾文看到了同樣的環境裏物種千變萬化,極不相同的環境中又可孕育出相同的生物,那都不像是拉馬克理論所能解釋的。他懷疑物種變異是生物一代一代繁殖過程中發生的,於是他又開始考察動物的配種。他搜集回來的資料雖然仍有不少是荒誕的─例如因病丟掉牴角的母牛生下的小牛也沒有角,但他卻能從這許多質素不一的資料中,得到生物經過累代交配繁殖,可產生巨大品種變異的結論。
不過,在人工配種的運作裏,人類執行了品種的選擇;那麼,自然界的野生動植物,經過隨機交配,繁殖出異種之後,誰來負責優選劣汰呢?
1838年10月,達爾文在日記本上寫着:“我偶然閱讀馬爾薩斯(T. Malthus)的人口論,目的完全是為了自娛。……我很能領悟到書中述及到處可見的生存鬥爭,並猛然悟到,在這種情況下,適應環境的變異品種較會得到保存,而不適應的則會被淘汰掉。”
達爾文便是在這偶然的情況下,找到了他需要的第三條線索,與其他兩條交互纏結,渾然築構成他的物種起源學說。博物學與人口學裏不同範疇的兩組思考,就在達爾文閒適閱讀之際,驀然組合,出現了“偶聯作用”,達成了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