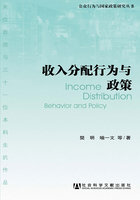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收入分配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始于周平王东迁以后。相对于西周周天子“天下共主”的权威而言,东周以后周王室名存实亡,国家控制权向各个诸侯国转移。生产力发展,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革命拉开序幕。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土地、人口战乱不断,相继出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社会制度由奴隶社会向土地私有农业社会(即传统文献中所说的封建社会)过渡。地主阶级兴起,到了战国末期土地买卖已经相当普遍,富人大量获取土地,贫富差距拉大。这一时期,由于诸侯国的竞争以及人才相对自由的流动,思想自由较少受到统治者的压制,由此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应运而生。各个学派纷纷开山立说,对国家的治理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也包括收入分配的思想。本节以赵晓雷(2007)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为主要参考对各家收入分配有关的思想进行梳理并加以评析。
一 儒家收入分配思想
儒家学派在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以孔子(前555~前479年)、孟子(前372~前289年)、荀子(前313~前238年)为代表人物。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一直作为历代统治阶级宣扬的正统思想,其对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更具影响力。此外,儒家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塑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家思想对今天的中国仍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们先从孔子开始介绍儒家的收入分配思想。孔子的收入分配思想散见于《论语》中,概括起来有如下思想。
第一,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孔子关于收入分配最为著名的言论。在《季氏将伐颛臾 》一文中,子路、冉有求见孔子。孔子责骂二人:“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并且指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认为,国家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分配不均。当然,“均”“和”绝非将富人和穷人的财产平均。孔子主张维护周礼,均贫富不是劫富济贫,而是通过建立一种规则,保证富人的权益,保证贫者的基本生活。
在此涉及孔子的利义观:“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春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试图通过伦理观对财富获得的方式加以限制,强调获得财富以及消除贫穷都应遵守道德。这样,社会即便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也不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
第二,藏富于民。
孔子主张“仁政”。在财政方面,他主张“敛从其薄”,藏富于民。当子冉向孔子问道如何治理国家时,孔子毫不犹豫地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同时,他意识到了保护税源的重要性,主张十一税,即税率为十分之一。反对统治者加重人民负担,主张在保护税源的基础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藏富于民促进人口增加,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税源则间接增加了国家财富。不过,十一税将劳役和军赋排除在外,并不足以反映人民实际的税赋负担。但孔子的低税赋、藏富于民的思想对于后世“轻徭薄赋”的财政税收思想有着先导意义。
孟子在儒家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尊为“亚圣”,其民贵君轻思想具有浓厚的民主色彩,分配思想和孔子一脉相承。
第一,民本思想。
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德治思想,形成仁政学说,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而民本思想,则是孟子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在孟子看来,没有恒产,人们的生活便没有保证,人们就不会遵守礼义道德,便会引起国家动乱。由此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主张。“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制”,即规定,限制。具体来讲,“恒产”即维持一个八口之家的农户生活所需的生产资料。以“恒产”保障农民自身基本消费,保障民心和社会的安定,由此实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也”的和谐社会。
孟子的“恒产论”的范围包括了农工商业的财产,但没有确切地提出工商业者财产如何处理的问题,只是为无财产的农民“制民之产”以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
第二,井田制。
井田制是孟子关于土地制度的理想设计。但孟子的井田制主张也包含着其通过平均地产实现收入平均的分配思想。井田制的基本思想是,“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共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井地关系到“谷禄”是否平均合理,关系到社会生产资料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要实现井地之均,首先必须“正其经界”,“经界既正,则分田制禄可坐也”。
那么,如何“正经界”?孟子提出“井田制”的方案。不过孟子同时也说“此其大略也,夫若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也就是说,这只是个设想,具体怎么做,就看国君你的了。在农耕社会,耕地面积是造成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因素。通过井田制将土地平均分配,实际上是通过土地的平均来实现收入的平均。
第三,按等级分配。
孟子主张按等级分配收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孟子·万章下》)这是孟子著名的世卿世禄的五等爵制。在此他明确指出了不同等级的人应分得有等级差别的土地和俸禄。
荀子对儒家典籍重新整理,其分配思想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兼足天下。荀子消除了前人在“富国”与“富民”上的矛盾,将二者在理论上有机统一起来,提出了“兼足天下”的观点。他认为,“富国”与“富民”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只要通过适当的途径便可实现民富君足的共同增长。为此,荀子提出“强本节用”的主张,即发展社会生产。“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下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荀子的“强本论”是中国重农思想的典型代表,他认同工商业也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行业,但同时也提出“工商众则国贫”,坚持农业是财富创造的唯一源泉。
“开源节流”是荀子“兼足天下”的另一项方案。一方面,要求放开政策,让百姓手中有充足的资源;另一方面,要求节制政府的财政支出,双向缩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贫富差距。荀子主张全面的轻税政策,通过“裕民”来达到富国的目的,“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民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荀子·富国篇》)。他认为,通过横征暴敛收取赋税无异于“求富而丧其国”的自杀行为。
第二,明分使群。“明分使群”是荀子的另一项分配原则。“分”即分工,“明分使群”就是希望人们能够明确自己的分工,并且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农民、商人、百工、士人分别根据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来获得酬劳,各尽其职,各得所获。
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收入分配思想一脉相承,皆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事而有得。孟子和荀子认识到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相继提出社会分工分配财产的主张。与孔孟不同的是,荀子理论上将富国与富民统一起来,更进一步走向了儒者所向往的大同社会。
二 墨家收入分配思想
墨家学派创始于战国时期,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且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创始人墨翟(前468~前376年),春秋末战国初期宋国(今河南商丘)人 ,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年代,墨家学派地位显赫,与儒家学派分庭抗礼,社会上流传着非儒即墨的说法。
1.有财相分
同孔孟的分配观相似,墨子也提出了“分财不敢不均”(《尚同中》),其所谓的“均”也并非完全的平均,而是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非命·下》)
墨子主张“有力相劳”“量功而禄”。“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尚贤·上》)不在乎人的身份地位,有能者就要受用,就得有所得,这点与儒家的“义然后取”有相通之处,但却是建立在无贵无贱的基础之上。墨子认为,生产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基本手段,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反对“不与其劳,或其实”。
墨子还提出财富的再分配思想。“多财则以分食”,“有力者度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然而墨子在此并没有指出明确的措施,更多地寄希望于“有财者”的道德觉悟。
2.轻赋税
墨子主张按适当比例收取赋税,认为赋税是统治者维持各级政府机构运转的经济来源,但征税应当满足“官府实”“万民富”的原则。统治者应当适可而止,不能通过横征暴敛来满足自身的奢侈消费。“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尚贤中·第九》)另外,赋税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即“加税”与“加利”同步,即墨子“交相利”的原则。
墨子的经济思想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其“量功而禄”的思想首先突破了儒家的阶级观念,其财富再分配等思想,“加税”与“加利”同步的赋税原则,在两千多年后的当今看来,也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 《管子》的收入分配思想
《管子》一书记载了中国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由其继承者收编整理而成,是先秦诸子时期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现存76篇中有2/3涉及经济问题,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方面均有论述,是中国论述古代国家经济最全面、最丰富的著作。
1.富上而足下的财富观
在财富分配上,管仲学派坚持“富上而足下”。“过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管子·牧民》)“民恶贫贱,我富贵之。”(《管子·牧民》)管子认为,天下治平首先要富裕国家才能吸引远方的人民前来归附。同时强调富民的重要性:“明王之务”在于“使民可富”,使人民富裕起来,保障其基本生活,继而实现长治久安。他认为富国与富民是一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足民有产,则国家丰矣”(《管子·重另》)。
管子认为,劳动和土地是财富的源泉,同时还建设性地提出了只要维持人地之间适当的比例关系便可实现“富上而足下”的目标。“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管子·八观》)“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管子·霸言》)根据当时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他们计算出每人三十亩耕地是实现“上富而下足”的人地之间的适当比例关系。
2.均地分利的土地制度
管子认为,土地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之一,因此十分重视土地制度改革。他认为,人民有了土地后便可自给自足,“田备然后知民可足也”。他还提出“均地分利”与“与之分货”的主张。“均地分利”即将土地经营使用权进行平均分配,通过均地,将各类土地折合成一定面积的耕地,然后将耕地均分给农民耕种,即“分利”。“与之分货”指的是劳动者将自己劳动的剩余产品上交给国家,将劳动必需品留给自己。所谓“分货”,实质上是农民向国家缴纳实物地租的过程。
3.赋税观
管子的经济思想是超前的,在当时甚至是精湛而有洞见的。美国兰德雷斯(2011)所著《经济思想史》,将《管子》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提并论。
管子将国家的赋税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直接税具有强制性,如土地税、房屋税、人头税等。但管子认为,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管子·轻重乙》)的间接税。“官山海”是间接税的典型代表,只要国家垄断盐铁经营,稍提高价格即可取得大量收入。这里,“海”指盐,“山”即铁。直接税因强制收取具有一定负面效应,但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却能让百姓只看见国家给他们的好处,而看不到夺取行为而自愿缴纳。
管仲学派也提出轻税主张,“取之有度”,“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管子·幼官》)。同时取消重复税,“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管子·问篇》)。
《管子》是先秦诸子时期的一部经济思想巨著,凡研究古代经济思想者,莫不首推《管子》。其富国富民并举的财富观,均田分力的土地制度,取之有度的轻税政策以及间接税政策,都是春秋时期中国伟大的经济学思想,仍可启迪于当下。
四 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其思想源于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则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关于财富分配的思想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按功行赏
“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商君书·错法第九》)也就是说,英明的君主在使用他的臣子和人民时,重用他们,一定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功劳,奖赏他们一定要加在他们的功绩上。论功行赏原则明确,那么民众就会争着立功。治理国家能让民众争着立功,那军队就强大了。“农战”是商鞅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按功行赏的分配政策则是商鞅“农战”发展农耕,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之一。
2.弱民强国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这是商鞅农战论的另一重要手段。商鞅认为财富是有限的、相对的,人民的富有必定导致国家的贫穷,所以一定要弱民。如果使百姓贫困,那么以功行赏的小恩小惠就会成为巨大的诱惑,“农战”便可以发展。
3.重赋敛以富国
韩非子在富国与富民这个问题上比商鞅更为偏激。“欲利尔身,先利尔君;欲富尔家,先富尔国。”同时,他提出“以农富国”的主张,且十分重视农业税收。“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韩非子·六反》)韩非子反对轻税,主张重赋敛以富国,坚决反对“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的做法,延续商鞅“弱民”的主张,希望通过重税实现“论其税赋以均贫富”。
法家思想与其他学派有明显区别。商鞅认为,国家要强大首先必须要“弱民”,并且从弱民的角度提出了“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商君书》)的用人主张,认为流氓是当官的最佳人选。韩非子坚持要求百姓“力尽于事”,然后“归利于上”,通过重农厚敛的手段来达到富国的目的。
五 道家
道家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以道、无、自然、天性为核心理念,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据此提出无为而治、以雌守雄、以柔克刚等政治军事策略。
道家对收入分配并没有专门的论述,其收入分配观可从道法自然引申概括。“道”指的是宇宙的本源和实质,可引申为事物的原理、原则、规律。既然如此,分配自然是道中一门,顺应其自然规律自是最好选择。“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七十七章》)人之道与天道相悖,常常是使富有的更加富有,贫穷的更加贫穷,这是不符合天意的。过多的制定政策只会越走越偏,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平衡的,经济规律若是能够完全地顺应自然规律,才能使经济达到自然环境中的那种生态平衡。“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道德经·三十二章》)上天降下祥瑞的甘露来滋润万物,总体上均匀分布,这是自然法则,根本不需要人为分配。
道家本身主张的便是天道无为的思想,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只要遵循自然规律,所有的问题都可顺利解决。“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认为,统治者征收重税是自取灭亡的途径,“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圣人不积”,也就是说圣贤的君主不必积累财富。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除法家和道家外,各家的分配思想虽各有特点但实则大同小异。各家皆提出了“均地”的主张,但所谓的“均”也都非绝对的平均,都主张“轻税”,不过在赋税对于国家的意义上观点倒是各有千秋。各家对于劳动与收入关系的看法也颇为一致,不劳而获是不正确的,商鞅也提出了按功行赏的观点。在富国与富民的问题上,法家独树一帜,主张“弱民强国”,并且,韩非子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赋敛以富国”,“根据赋税均贫富”的主张。而道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打开了收入分配的玄妙之门,只要遵循“道”,顺应规律便可无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