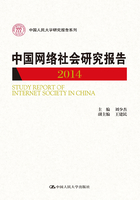
三、从集体表象到社会表象的提升
虽然缺场的网络化的社会认同因其匿名性、脱域性和扩散性等特点而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大量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但就其总体趋势而言,缺场的社会认同对全球化和个体化两种相背趋势对立并存的当代人类社会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正像福山在《大分裂》中论述的那样:“正当西方社会的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之时,却出现了这样一些负面的社会趋势;这些趋势说明,西方社会中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变弱。”![[美]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93162A/14676544005848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7196187-emIFwKyc8ILbg9bmY9OPhI5NsPjy9T8S-0-e2dd51de1ac2f63a035147126ebdd854) 福山所说的负面的社会趋势,是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发生的个体化趋势。这种使工业社会的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弱化甚至解体分裂的个体化趋势,是以网络信息技术支持的个体化工作方式的形成为前提的。正是个体借助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信息技术,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工作空间和工作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追求个体价值、个体地位和个体自由的价值原则,才导致了工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价值体系的大分裂。
福山所说的负面的社会趋势,是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发生的个体化趋势。这种使工业社会的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弱化甚至解体分裂的个体化趋势,是以网络信息技术支持的个体化工作方式的形成为前提的。正是个体借助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信息技术,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工作空间和工作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追求个体价值、个体地位和个体自由的价值原则,才导致了工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价值体系的大分裂。
福山论述的这种社会分裂现象,在工业化处于上升时期的20世纪初也出现过。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等著作中论述的社会分化问题也具有价值体系分裂、社会秩序遭遇尖锐挑战的严重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团结,涂尔干给出的诊断是开展道德教化、整合价值观念,进而避免社会分裂。针对经济学和斯宾塞单纯鼓励个体竞争、加剧社会分化甚至社会分裂的片面性,涂尔干主张培育集体观念、促进社会团结。所谓集体观念就是在人们可以开展直接交往的社会群体中形成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宗教行为规则等共识,而这种共识是介于逻辑思维和本能冲动之间的感性表象,涂尔干称之为集体表象。
把能够维持群体团结的共有观念理解为感性表象,这一点对于实现社会整合的追求十分重要。因为涂尔干是在社会整体意义上来思考社会团结问题的,所以他一定要找到能把广大社会成员整合起来的思想观念,而这种思想观念既不能是理论层面的逻辑思维,也不能是本能无意识,只能是广大社会成员头脑中经常存在的感性意识。涂尔干认为,感性意识可以对社会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因为感性意识直接同具体的日常社会生活相对应,他说:“在所有能够产生这种强烈效果的事物中,首先应属我们的反向状态所造成的表现。实际上,这种表现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现实图像,也不是事物映射给我们的死气沉沉的幻影。相反,它是搅起机体和生理现象之波澜的力量。”![[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5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93162A/14676544005848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7196187-emIFwKyc8ILbg9bmY9OPhI5NsPjy9T8S-0-e2dd51de1ac2f63a035147126ebdd854) 引文中的表现(representation),应当译为表象。从心理学和认识论的角度看,表象是感性认识的一种形式,即在感觉和知觉基础上对认识对象的形象性、回忆性再现,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度反观性、概括性和能动性的感性认识。
引文中的表现(representation),应当译为表象。从心理学和认识论的角度看,表象是感性认识的一种形式,即在感觉和知觉基础上对认识对象的形象性、回忆性再现,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度反观性、概括性和能动性的感性认识。
在涂尔干看来,并非像机械唯物主义者所论述的那样,表象是对事物的机械的、照镜子式的反映,相反,表象具有能动作用,可以作为支配人们身体及其行动的活生生的力量。“它非但是能够产生观念的一种神经流,从大脑皮质的原发点中流出,从一个神经丛流向另一个神经丛,而且在运动中枢里不断产生振动来确定我们的运动,或者在感觉中枢里不断产生振动来唤起我们的意象。”![[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5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93162A/14676544005848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7196187-emIFwKyc8ILbg9bmY9OPhI5NsPjy9T8S-0-e2dd51de1ac2f63a035147126ebdd854) 并且,涂尔干进一步指出,表象因为是形象性的意识,它能产生比抽象观念对身体行动更大的支配力量。表象能对人们产生较大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它把形象意识直接同具体事物联系起来,进而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明确的支配作用。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涂尔干把整合社会、促进社会团结的希望寄托于表象。
并且,涂尔干进一步指出,表象因为是形象性的意识,它能产生比抽象观念对身体行动更大的支配力量。表象能对人们产生较大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它把形象意识直接同具体事物联系起来,进而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明确的支配作用。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涂尔干把整合社会、促进社会团结的希望寄托于表象。
虽然涂尔干将其讨论的表象说成集体表象,但他期望的是社会共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信念,因为他一直惦念的是社会的整体团结。于是,在涂尔干那里也存在把社会的共有观念归结为集体或群体观念的问题。这与社会心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试图把群体认同等同于社会认同的问题相同,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结构论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如前所论,结构论研究方式的重点在于揭示事物的内在构成,个体与群体是社会最明显的构成要素,涂尔干作为结构论传统的奠基人,尽管一再强调社会学研究整体社会,但结构论的眼光限定了他一定会把主要注意力聚集到个体与群体之上,当他反对个体主义的狭隘性时,从群体出发就是最接近的途径。
同时更重要的是,涂尔干对交往实践的研究重视不够,而社会整体只有在交往实践中才能看清楚,所以,尽管强调社会整体关注,但实际上看到的只是社会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动态的现实社会本身。这或许与社会的发育程度有关,涂尔干的时代,工业社会正处于上升时期,组织化、制度化、市场化等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得以成功的基本经验,也是涂尔干认识的工业社会的基本事实,而这些正是他强调职业群体意识或集体表象的根本原因。
到了网络化时代,人们凭借计算机、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等新媒体技术,不仅超越了在确定的制度规范限制中的企业组织和社会群体,而且超越了城乡社区,进入全民族社会空间乃至全球社会空间,一个动态活跃的、充满生机且不断扩展的网络社会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于是,社会认同的展开空间和认识社会认同的研究视野也逐渐明确地从个体、群体进入到了社会。如果直面网络交往行为中的社会认同,不难发现网民们表达的大量社会认同是在表象层面展开的,特别是在新浪微博这样一类短小而快捷的网络交流中,网民们表达的信念与评价、赞同与否认、接受与排斥等,鲜见逻辑推论和量化计算,大量的是感性层面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在广大网民中形成了超越个体和群体界限的社会表象。
网络交往中形成的社会表象,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表象,可以简称为网络社会表象,因为参与网络交往的网民尽管受到不同程度的个体和群体的限制,但他们可以匿名或前台匿名地在网络中表达观点、沟通意见,进而形成超越自身和群体限制的共同表象。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网络行为是交往实践,它展开的交往关系不仅体现了社会的本质,而且也是社会主体的表现形式或现实存在。因此,网络社会表象不能理解为是个体表象及群体表象的汇集,而是有着自身主体(社会主体)的感性意识,并因此而具有与个体表象和集体表象不同的特点和功能。
网络社会表象最明显的特点是动态性。传统心理学和认识论谈及感觉、知觉和表象等意识形式时,通常认为表象是感性意识中最稳定的形式,因为表象不仅是在相对完整的知觉形象意识上形成的,而且还能被形象地再现或回忆。网络社会表象也具有这种相对稳定的特点,但因为它是在无数个体参与的无边界的动态交往中形成的,所以网络社会表象既可能呈现为不断的扩展延伸过程,也可能呈现为渐进趋稳并最终沉寂湮没的过程。那些引起很多网民关注和参与的网络事件,一般都经历了兴起、高潮、衰落和沉寂几个环节,在兴起和高潮两个环节中,随着网民的积极参与和网络信息的进一步传播,网络社会表象呈现为扩展延伸过程;而在衰落和沉寂两个环节,随着网民围观热度的降低和网络信息传播的收缩,网络社会表象呈现为渐进趋稳并最终沉寂的过程。
在扩展延伸过程中,网络社会表象具有个体表象和集体表象无法与之相比的巨大的社会整合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当涂尔干试图通过集体表象实现社会整合的理想时,他已经意识到集体表象的限制性。因为集体是有边界的,并且各种集体表象过于强烈时,还会因为它们固守自身而相互排斥并引起社会分裂。只有在网络交往中形成的社会表象,才能既表达个人意愿又在交流互动中超越个体局限。
网络社会表象可以引起网络兴奋,它可以使网络动员进入高潮。涂尔干论述集体表象时曾谈及集体兴奋,在宗教活动中,神职人员通过各种生动、形象而神秘的演说,努力引发教徒集体表象的生成并刺激教徒形成集体兴奋。热烈的集体兴奋不仅可以用来开展宗教动员,实现宗教群体的有效整合,而且可以引发激烈的宗教行动甚至残酷的宗教战争。网络社会表象引起的兴奋是超越了个体和群体边界的社会兴奋,它凭借网络信息传递可以穿墙透壁、无孔不入的能力,把散存于不同角落中的个体乃至不同制度体制限制下的群体的兴趣和意象吸引、集中和调动起来,不仅在网络交往中形成共识,而且还可能引导各种场域中的实际行为发生联结甚至大规模的群体行动。近年发生的“保钓游行”、“肉铺募捐”、“周口平坟事件”等,特别是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网络反腐”,其中都充分地显示了网络社会表象引起集体兴奋并实现大规模社会动员的强大作用。
有效的网络动员,特别是引起社会兴奋甚至社会运动的网络动员,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整合。尽管有时网络动员的结果并不一定像实体权力机构所期望的那样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可能是不断变化的状态,但这不能掩盖其积极的社会整合的作用。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统治者或社会管理者一直试图通过法律制度和组织纪律规定社会成员的行为,以便实现整合社会、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应当承认,这种理性的制度规定在过去的历史中已经被证明具有明确效力,但在网络化时代的今天,这种相对静态的社会控制手段对于维持社会整合,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了。清醒地认识网络社会表象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作用,既是把握网络社会变迁的重要问题,也是促进社会整合、稳定社会秩序不可缺失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