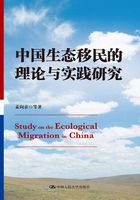
第三节 生态移民的迁移选择性
迁移选择性主要是指迁移人口通常具有不同于迁出地非迁移人口的特征。迁移人口与非迁移人口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影响,一直是人口学家研究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方面。莱文斯坦在最早的人口迁移理论研究(Ravenstein,E.,1885,1989)中就曾提出过,在短距离人口迁移中女性占主导的有关性别选择的结论。Lee在他的《迁移理论》一文中,更是对迁移选择性进行了专门的阐述:“迁移是有选择性的,移民并不是迁出地人口的随机选择。这是由于移民对迁入地和迁出地推拉因素的反应和克服迁移中间阻碍因素的能力是因他们的个人特征而不同的。”他继而指出,主要对迁入地的拉力做出反应的移民通常是正向选择,而主要对迁出地的推力做出反应的移民通常是负向选择。移民的特征通常会介于迁出地和迁入地人口特征之间(Lee,1966)。迁移选择性也在各国的迁移研究中被验证。通常,从年龄上看,劳动力年龄人口的迁移最为活跃;从性别上看则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从婚姻状况上看,单身、离婚和丧偶人口一般比已婚人口更容易发生迁移;从受教育程度上看,通常受教育水平越高,迁移的可能性越大(Odland J.and Shumway J.M.,1993;姚华松、徐学强,2008;曹菁轶,2007)。从中国来看,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所做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口迁移具有较强的年龄选择性和教育选择性,但青年迁移者中,女性所占比例有所上升且呈现出高于男性迁移风险的态势。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人口迁移率较低,单身者迁移率较高(唐家龙、马忠东,2007)。
生态移民作为一种特殊的移民形式,其迁移选择性也具有自己的特点。不同地区不同的搬迁形式也有不同的迁移选择特点。对于整村搬迁的形式,可以说迁移选择性不强。但对于部分搬迁的项目,迁移还是具有某种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或者由于地方政府在选择移民时具有某种倾向性,或者由于移民出于某种考虑而具有某种共同特点。如我们在宁夏早期吊庄移民调研中了解到,最初迁移的人通常是较为贫困且在迁出地具有较差人际关系的家庭,他们更期盼在新的地方获得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各地以及不同时期迁移选择性具有不同特点,鉴于资料的可获取性,我们尚没有能力总结所有的这些特点。下面将用我们在三江源生态移民村的调研资料,分析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迁移选择特点,虽然不具有全国的代表性,但可以分析具有移民具有选择权的情况下生态移民的选择性特点。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数据允许的条件下,同样可以用于其他生态移民项目的迁移选择性研究。
三江源生态移民迁移形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迁移,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的选择性不会像自由迁移那么显著。但是三江源生态移民是在政府号召下的自愿选择,即移民对自己是否迁移拥有选择权。因此,我们可以考察这种迁移方式下的移民是否具有选择性以及其选择性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在国内以往的生态移民研究中还没有人做过。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的迁移选择性主要看移民与非移民特征的差别并比较移民与迁入地人口特征的差别。选用的指标是用于度量迁移选择性的差别指数(Indices of migration differentials)。
差别指数是国际上通用的度量人口迁移选择性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IMD=(Mi/M-Ni/N)/(Ni/N)
或者
IMD=(Mi/Ni-M/N)/(M/N)
其中,IMD为迁移差别指数;
Mi是具有某特征的迁移人数,M是总迁移人数;
Ni是具有某特征的非迁移人数或总人数,N是非迁移总人数或总人数。
第一种方法称为比重法,第二种称为比率法,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同(祝卓,1991)
如果迁移人口特征与迁入地或迁出地的非迁移人口特征完全一样,则迁移差别指数为0。迁移差别指数越大,说明迁移在迁出地的选择性或与迁入地的差别性越强。迁移差别指数的正负反映迁移选择在不同特征的分布状况。比如在年龄选择上,如果迁出人口劳动力人口所占比例较大的话,那么劳动力年龄的差别指数为正,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差别指数则可能为负。差别指数数值的大小反映迁移选择的强烈程度,正负反映的是选择的方向性。
本章主要想考察这种差异对生态移民效果的影响,因此,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指标的重要性,主要选取生态移民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结构与规模、家庭草场面积、牛羊头数、经济收入水平、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和民族结构等指标进行计算和分析。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自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有关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人口指标以及青海省统计年鉴中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社会经济指标。很遗憾,我们没有全面的移民状况的数据,有关移民的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信息来自课题组2009年7月在青海几个移民村的调查资料和部分移民村的移民规划资料。出于课题承诺的保密原则,我们将只给出这些移民村的地点而不给出这些村的具体名字,它们的名字将用一些符号代表。这些移民村包括黄南藏族自治州的由泽库县迁到同仁县的“移民村A”(这个移民村属于跨县搬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同德县尕巴松多镇的“移民村B”(县内迁移)和由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迁入同德县的“移民村C”(跨州迁移);另外还有玉树藏族自治州迁入称多县黑河乡的“移民村D”(县内迁移)和迁入格尔木市郊的“移民村E”,后者属于距离更远、跨度更大的移民搬迁形式。这几个移民村涵盖了各种类型的迁移形式,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但各个村的资料并不相同,在下面的分析中会具体指明。
二、三江源生态移民迁移选择性分析
(一)移民年龄选择性
从计算结果来看,移民的年龄选择性跟我们的假设相同,从迁入地和迁出地两方面来看,移民的迁移差别指数都比较小,这说明移民的年龄结构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年龄结构差别不大。这尤其在近距离的县内迁移和同区的县际迁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说明不仅移民的年龄选择性不强,而且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年龄结构差别最大的是迁移到格尔木市的移民村E。其少儿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的迁移选择差别指数分别为0.43、-0.21和1.40。这主要是由于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差别较大。迁出地曲麻莱县还是典型的以牧业为主的牧区,而格尔木市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其人口出生率远远低于迁出地,人口年龄结构也呈现出较大不同(见表4-1)。
表4-1 生态移民的年龄差别指数

资料来源:五个移民村的实际调查数据。
(二)移民性别选择性
从计算结果来看,生态移民的性别比基本都略高于迁出地的人口性别比,亦即迁出的男性比例还是略高于非迁移的男性人口比例。但除了移民村B和移民村C人口性别比超过了110外,其他移民村的人口性别比与非移民的人口性别比差别并不大。迁移差别指数多在0.1以下。移民的人口性别比也略高于迁入地的人口性别比,只有迁入格尔木市的移民村E的人口性别比低于格尔木市原住民的性别比。这主要是因为格尔木市是个移民城市,移民中的男性比例较高,因而格尔木市的总人口性别比较其他人口迁入地要高(见表4-2)。总体来说,生态移民还是略有一点性别选择性,即男性迁移者更偏向于迁移,但这种选择性并不显著,因为毕竟迁移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表4-2 生态移民的性别差别指数

资料来源:同表4-1。
(三)移民家庭规模与结构
从计算结果来看,移民平均家庭规模在各个移民村都呈现出了比较一致的特征,即移民村的平均家庭规模均小于迁出地的平均家庭规模。差别指数都在-0.2以上(见表4-3),移民村D的平均家庭规模只有2.2人,只是称多农村平均家庭规模的一半。从家庭户结构看,多数家庭为3人以下的小家庭。如移民村A中,一人户家庭占移民家庭的比重为10.1%,两人户家庭占20.2%,三人户家庭占26.7%,三者之和接近60%。四人户家庭占25%。五人以上的大家庭只占18%。数据结果和我们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致的。在调查中,当地干部群众告诉我们,由于移民补贴是按户发放,因此,在迁移前有些大家庭采取了分户的办法,即把部分成员分离出来另立门户,这样,家庭中部分成员可以留在原地享受牧区的草场牛羊,部分成员变成移民可以享受到移民的住房和补贴。这样做也并不完全是出于自私的考虑,主要原因还是迁移的推力不足,很多牧民不愿意离开世世代代生活的牧场,没有迁移的动力。
表4-3 生态移民的家庭规模差别指数

资料来源:同表4-1。
(四)家庭拥有的草场和牛羊数量及经济状况
移民家庭拥有的草场面积和牛羊数量也是我们关心的重要指标。因为移民的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只有拥有足够大的草场面积和足够多的牛羊的家庭移出来,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由于我们没有所有移民家庭的迁移前草场面积、牛羊头数的资料,因此这里只用我们拥有这一数据的同德县为例。移民家庭搬迁前拥有的平均草场面积只有500亩,而同德县牧民家庭拥有的平均草场面积为3564亩。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移民村中还有大量原本就是做生意或小买卖的人,甚至可能是退休人员、国家职工等,这些人搬迁前其实根本就没有草场或牛羊。移民家庭移民前的经济收入也远低于迁出地的平均水平。同样以同德县为例,移民搬迁前的月家庭平均收入为797元,而当地牧民的平均月收入为2517元。这是在各个移民村发现的普遍现象。只有草场少、牛羊少、收入低的贫困家庭才更愿意迁移。而一些草场牛羊大户更愿意留在牧区,因为他们每年放牧的收入要远高于搬迁后国家所给的补贴。同时,当地政府也不希望牛羊大户搬出,因为这会影响其牧业发展和产值增加。
(五)移民的教育选择性
移民的教育选择性是自由迁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通常教育水平高的人会更倾向于迁移,因此,移民的教育水平会高于非移民的教育水平。但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教育选择性不明显。从表4-4我们可以看出,移民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15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多在50%以上,有的移民村甚至超过了60%。移民的文盲比例与非移民相近,有的甚至超过了非移民的文盲比例。移民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比例均低于10%,不仅低于迁入地的总体教育水平,而且低于迁出地的总体教育水平。在近距离的生态移民迁移中,这种差别还不是特别明显,差别指数还都在1.0以下,但迁到格尔木市郊的移民村E的文盲率为53.4%,远远高于格尔木市的14.3%。巨大的教育水平差距,使得移民在后续的就业和生活生产适应上面临重重困难。
表4-4 生态移民的教育差别指数


资料来源:同表4-1。
(六)移民的民族状况
三江源生态移民几乎是清一色的藏民,多数祖祖辈辈生活在海拔很高的牧场,靠放牧为生。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只会讲藏语,既听不懂汉语,也不会说汉语。而无论是迁到镇上、县上还是格尔木市郊,他们都已经不再拥有牧场、牛羊和土地,他们传统的生存技能在迁入地完全派不上用场,面临着生产方式、生存方式和文化习俗等全方位的改变。而语言不通,又使得他们的转变举步维艰。即使同是藏民,不同地域的文化习俗也存在很大差异,跨州县的移民迁移比县内迁移的融入和适应更加艰巨。最极端的是迁入格尔木市郊的移民,虽然迁出地和迁入地政府都想尽了各种方法帮助他们尽快适应迁移后的生活和尽快找到就业的渠道,这种努力至今仍然事倍功半。很多移民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只好重回高原继续放牧。
三、三江源生态移民迁移选择对移民效果的影响分析
三江源生态移民既不同于人口的自由流动,也不同于完全没有自由的工程非自愿性移民,而是一种移民有选择性的非自愿性移民形式。因此,其迁移选择性也与自由移民和完全非自愿的工程移民不同。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因此移民的性别、年龄选择特征不明显。移民的教育水平选择性也不强。移民村的移民文盲率很高,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寥寥无几。但每个移民村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平均家庭规模都小于迁出地的平均家庭规模,一人户、两人户移民家庭占很高的比例,五人以上的大家庭迁移的比例很小。另外,从移民迁移前的经济状况来看,迁移者多数是拥有较小草场面积、较少牛羊头数、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贫困的家庭。
不同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扶贫开发移民,三江源生态移民属于为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而实施的生态移民,虽然提高移民的生活水平也是迁移的目标之一,但迁移最根本的宗旨还是迁出地的生态保护和恢复。从前面分析的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迁移选择性特点来看,无论是移民较小的家庭规模还是较少的草场和牛羊头数,都不利于最大效率地实现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的目标。如果只是人口相对少的家庭迁移出来,那么对于迁入区来说,其接纳的任务是一样的,对政府部门来说,其投资也是一样的,因为移民的住房和补助都是按户进行的。但是,对于迁出地来说,相比于大规模家庭的迁出,其迁移效率显然会受到影响。另外,如果迁移家庭迁移前只拥有较少和较差的草场以及较少的牛羊,甚至有的根本没有草场和牛羊,那么这样的迁移对缓解迁出区的载畜量和生态压力也是杯水车薪。
造成这种移民选择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推力相对不足。虽然从外人的眼光看,三江源地区地处高寒地带,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但对于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牧民来说,这里是他们宁静而美丽的家园,是他们生命依托的地方。他们有自己和大自然相处的方式,有自己保护生存环境的独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精神的寄托。在我们对移民原因的调查中,认为由于迁出地条件太差、生活太苦而迁出的比例只有8.9%,认为为了保护迁出区的自然环境而迁移的比例只有17.6%。
二是拉力有限。虽然政府给每个移民家庭建好了住房,并配备了水电道路等各种基础设施,但一年每个家庭6000元的生活补贴并不足以吸引大家庭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迁移。在迁入地,移民没有草场和土地,他们原来的生产、生活技能将无法发挥作用,况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面临语言、生活习惯、文化、宗教习俗的一系列变迁,这些都是阻碍移民迁移的巨大障碍。因此,面对政府的移民政策,许多家庭采取了避重就轻、减少损失的策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移民迁移原因占首位的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这说明政府的倡导是迁移的决定性因素。另外,迁入地拉力中,选择最多的是为了子女受到更多的教育,这说明有部分牧民家庭已经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因为迁入地的教育条件通常好于迁出地的教育条件。所以,我们看到移民村中老人带孩子以及妈妈带孩子在迁入地生活的情形非常普遍。对于相对贫穷的家庭来说,他们迁移的损失相对较少,到了迁入地,有了政府的补贴和各种优惠的就业政策和培训,或许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线转机。
四、建议与结论
为了保护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国家以及青海省政府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生态移民工程也按照计划在逐年实施,一座座移民村建立起来,一批批牧民被搬迁出来。成效看似显著。但移民村的数量和移民的人数并不是迁移的目的所在,迁移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从前面我们分析的移民的迁移选择性特点来看,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目标的实现远非看起来那么简单。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的过程中认真考虑。
首先是迁移的目的性需要明确,项目本身以及迁移人数并不是目的,项目的根本宗旨是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从这个目的出发,迁移家庭的人口规模,草场面积以及牛羊头数等,都应该有个相应的标准。另外,移民迁出后,他们退还的草场的生态恢复和保护也应该有具体的落实措施和评估监测机制。
其次,如果想吸引更多的拥有较多草场和牛羊的家庭迁出,应该适当加大迁入地的拉力。目前一个家庭一年6000元的补贴,尚不足以吸引经济条件好、收入高的家庭迁出。而且政府补助是按户而不是按人发放的,这样,对于大家庭来说也就无形中起到了一种屏障作用。
另外,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生态移民,由于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方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习俗的巨大差异,三江源生态移民面临的挑战也无比巨大,如何让移民尽快适应迁入地的生活,找到他们谋生的新方式,依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巨大难题。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长距离和差异大的迁移,更会加大这种转变和适应的难度。其实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同样需要人们来保护和看守。当地群众和官员曾经提出,可以考虑通过政府补贴减少载畜量来缓解三江源地区的人地矛盾和人畜矛盾,并逐渐加大保护环境的宣传力度和提高牧民的教育水平,这样可以水到渠成地变移民的被动迁移为自发迁移,不失为一种更有效率和稳妥的办法。
同时,在考虑保护迁出地的生态环境的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迁入地的生态保护问题。从大的三江源地区来讲,移民迁入地同样属于三江源地区。迁入地移民村的建设、移民的后续生产生活的开展,同样要对迁入地的生态环境构成威胁和破坏。两者孰轻孰重,在进行移民规划之时即应该考量清楚。
总之,三江源生态移民由于地域和民族的特殊性,其迁移效果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易于评判和下结论。移民工程牵涉各级政府部门、迁入地、迁出地以及移民家庭方方面面,因而在决策和实施的过程中应该慎之又慎。
从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迁移选择性的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搬迁,由于移民具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迁移依然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这对移民以及生态移民初始目标的实现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还需加强对生态移民选择性及其深层原因的探讨,并为以后的移民搬迁提供一定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