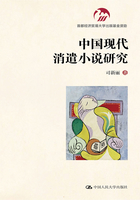
第三节 古之雅俗之分与现之严肃消遣之别
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存在两种不同的雅俗格局,因此规定了两种不同的文学面貌,但也存有一定历时性联系。
一、古代文学的雅俗之分
一些学者在研究古代雅俗文学之分时,往往提到“大传统”和“小传统”,余英时认为:“大传统或称之为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层的,而小传统或称之为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1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其实,中国文化中很早就存在雅与俗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与上述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是对应的,即雅俗的分野恰好相当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野。
雅的含义是什么?雅的本义是一种鸟,在秦地被称为“雅”。许慎的《说文解字》中释为:“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雅,楚鸟也。”章炳麟曾解释“雅”就是“鸦”,古代同声,发“乌”音,“乌乌”是秦地的特殊声音。而秦地是周朝王畿之地,所以雅声也就成为周朝王畿之声。从语义上看,“雅”是“正”的意思,“雅”又指“雅言”,雅言就是当地的京话和官话。余冠英在《诗经选》中指出:“雅是正的意思,周人所认为的正声叫雅乐,正如周人的官话叫做雅言。雅字也就是‘夏’字,也许是从地名或族名来的。”雅表示周朝王畿的特征,历代儒者、尊王都把雅作为正统,因此雅文化一直具有高贵、正统的特征,朱自清曾说:“雅是纯正不染。”
“俗”的含义是什么?应邵《风俗通义》解释为:“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释名》解释为:“俗,欲也,俗人所欲也。”(注:刘熙:《释名》,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说文解字》注:“俗,习也。”明代李开先在《市井艳词序》中提出俗文学特征:“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虽君臣朋友,亦多有托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谭帆根据“俗”的内涵和其组词的分类,把“俗”的含义分为如下几种:第一,如同“风俗”之“俗”,指习惯已久形成的风尚、习俗。如《说文解字》说:“俗,习也。”《荀子·强国》说:“入境观其风俗。”第二,如同“世俗”之“俗”,有和风俗相近之义,更为普遍的意思是平常、平庸的世人。如《老子》说:“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庄子·天地》说:“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墨子》说:“世俗之君子,视义士不若视负粟者。”《荀子·儒效》说:“有俗人者,有俗儒者。”第三,与雅俗的“俗”相关,这里“俗”即指与文雅之士相对的粗鄙之人,更多的是与文艺和审美相关联。第四,与通俗的“俗”相关,主要指特定的语体,这里的“俗”更明确地指普通老百姓。如《警世通言》第十二卷中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注:谭帆:《中国雅俗文学思想论集》,5~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总之,谭帆对“俗”的含义作了如下解释:“‘风俗’之‘俗’指称特定的风尚习俗,而风尚习俗又以民间性与下层性为主流;‘世俗’之‘俗’在道德、情趣和追求上划出了一个独特的人群,这一人群是以现实追求和俗世享受为特色的;‘雅俗’之‘俗’主要从审美和文艺的角度立论,指在思想情感、表现内容、风格语体方面与‘雅’相对举的、趋于下层性的文艺和审美的一脉线索,并在价值判断上作了限定;而‘通俗’之‘俗’既承‘雅俗’之‘俗’,又由‘世俗’之‘俗’演化而来,然更注重下层百姓之内涵。”(注:同上书,9页。)在“风俗”、“世俗”、“雅俗”与“通俗”四个义项中,“世俗”应是其本质属性。
李渔《闲情偶寄》中说:“诗文之词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总分明,词曲则不然,话则本之巷谈里语,事则取其直说明言……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在一定历史时期这种说法相对而言有一定道理。鉴于这样的认识,有些研究者认为可以从文体上划分雅俗,比如认为诗文归属于雅,小说戏曲归属于俗。从整体而言,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细究会发现诗出自民谣,那些不能称为俗的轻灵蕴藉的宋词也是出自词曲,鲁迅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可见,仅从文体本身判断古代文学的雅俗之分,显然有些不当。又有研究者认为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认为诗歌、小说等主要体裁都经历了一个由俗到雅的过程。并认为《诗经》中的国风由俗到雅,楚辞也是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而来,汉乐府民歌对唐诗的繁荣起到了很大作用;小说也是从野史和民间神话而来,到中唐时代传奇小说才可以登大雅之堂。因此认为“一切文学体裁最初都是通俗的,一切典雅文学最终都起源于通俗文学,最终又化俗为雅”(注:朱志荣:《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11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仅从纵向的发展判断一种文体的雅俗,也不是辩证全面的观点。其实雅俗之间并非一成不变,昨天的俗,可能成为今天的雅,今天的雅,可能成为明天的俗。中国的雅俗文学是一个动态系统,就《诗经》而言,《诗经》在春秋之前是俗文学,到了汉代首次成为雅文学;汉乐府是地道的俗文学,但到了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则成为雅文学;唐代兴起的词是俗文学,但等到宋代,词成为时代精神的表现者时,词便成为雅文学。(注:参见冷成金:《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266~27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相对于传统的诗、文、词,宋代兴起的小说一直到明清,都处于俗文学的地位,但小说界革命后,因小说地位的提高,这种局面被打破,于是小说便处于雅文学的地位。随着小说的发展变化,在这种文体内部又产生了雅俗的区分。
可见文学的雅俗都是相对而言,判断其雅俗应该有一定参照物,相互比照才能构成雅俗。总之,雅俗之间既相互比照、相互较量,又相互渗透、相互借取,在一定条件下还会相互融合、相互转化。古代文学到底有没有雅俗之分?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雅、俗各自的起源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谈起。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河流中,雅俗分野的情况须从先秦时代说起。最早把雅俗作为相对的概念放在一起的是先秦时代的雅乐和俗乐之分。先秦时期,把以政治伦理教化为目的的音乐和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音乐并列在一起,前者被用于宫廷进而赋予了雅的色彩,后者因传颂民间进而沾染了俗的色调。《诗经》由风、雅、颂组成,雅、颂多为王室、贵族之作,风多为民间歌谣,这大概是中国文学史上有作品为证的初始的雅俗分野。周王朝及其诸侯在很多场合要演唱诗篇,他们把诗乐合称,分为雅乐和俗乐,从文词方面看就是雅诗和俗诗。雅乐又称“先王之乐”,指符合礼乐规范标准的宫廷之乐,是正统音乐,能够符合儒家政治伦理教化审美观念,与士大夫的政治文学精神一脉相传;与雅乐相对的俗乐是指在民间兴起,流行于社会,但不符合雅乐标准而被排斥的世俗之乐或“淫靡之音”(注:《论语·卫灵公》:“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孟子·梁惠王》中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样对俗乐的理性认识。实际上这里的雅乐和俗乐分别代表了雅俗审美追求的最初形态,从而形成了上层士大夫和下层世俗不同的审美意识。李天道认为:“‘雅’与‘俗’审美观念的对峙突出地体现为阶级的分野。‘雅’的,属于统治阶级贵族、士大夫阶层;‘俗’的,则属于被统治阶级、平民百姓的,表现出一种道德与政治教化的对峙。”(注:李天道:《中国美学之雅俗精神》,225~22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有了雅乐与俗乐的区分,才有了雅俗审美追求的区分,也才有了对雅与俗的评价态度。由此推之,早期的雅俗审美意识中带有强烈的政治教化色彩。宋代朱熹的《诗集乐传序》中曾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也。”其实这更加强化了雅俗的分野。
雅俗的分野必然导致雅俗的冲突与对抗,这种冲突和对抗首先体现在雅俗价值体系的差异和审美观念的对峙上。价值体系的差异主要体现为精英审美意识和大众审美意识之间的对立。雅是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追求;俗是平民大众的审美追求。雅的审美追求表现了对俗的审美追求的批判和抗拒。审美观念的对峙主要体现为阶级的不同,雅的审美观念属于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俗的审美观念则属于被统治阶级和平民大众。其次体现在文艺思想方面的抗拒,表现出强烈的伦理与政治教化倾向。再次体现在文艺的审美要求方面,雅俗的区别表现在语言风格、艺术格调和意蕴方面。《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既是雅乐和俗乐的审美规范,更表达了对雅乐和俗乐审美特性的认识。
雅与俗,在中国美学史上是一对古老而新奇的概念,其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褒义与贬义之别。从广义看,“雅”属于统治阶级、士大夫精英文化层面,是正统的;“俗”属于被统治阶级、世俗大众文化层面,是浅俗、粗朴的。从狭义看,“雅”指审美意趣、审美境界上的高雅和庄重;“俗”指审美意趣、审美境界上的通俗和浅显。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看,雅俗之间都存在相互矛盾、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注:参见李天道:《中国美学之雅俗精神》,293~29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老子·二章》中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这说明了事物发展的根本特性,因此看待雅俗对立相融关系,要用全面的眼光,不能绝对化。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说“随俗雅化”,李渔在《窥词管见》中说“雅俗相和”,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卷十四中说“雅俗相兼”。这些都形象地说明了雅俗之间的关系。王国维认为:“雅俗古今之分,不过时代之差,其间固无界限也。”宋若云在《逡巡于雅俗之间——明末清初拟话本研究》中指出:“其实,考察雅与俗的关系,其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俗是雅所由诞生之处,而雅则是俗所运动的目标方向。”(注:宋若云:《逡巡于雅俗之间——明末清初拟话本研究》,26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总之,雅俗分野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存在确定无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立、相互融合、相互转化。比如荀子就提倡雅俗相互转化,他一方面推崇雅乐,注重雅乐的审美教化作用,一方面又注重俗文学,让人多听国风之声。再比如秦代改《武》乐为《五行》,汉代改《韶》乐为《文始》等,但因为长期动乱,原有的雅乐已经丢失,只能收集民歌民谣(俗乐)进行整理加工,这是化俗为雅,以俗为雅的过程。从雅俗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俗化可以雅化,雅化也可以俗化,但雅化的极致有可能是僵化。
从文学创作方面讲,雅文学和俗文学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具体到作品,雅俗是如何区分的?中国古代雅俗文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语言、体裁、表现手法等方面。首先,语言方面,中国古代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书面语与口语的分离,即有文言和白话的区分。文言深奥难懂,人们都以书面语(文言)为雅,把口语(白话)看作俗。从汉代到晚清文言一直占领雅文学的殿堂,被作为正宗,居于庙堂之上,而白话一直存在于俗文学中,居于庙堂之下,不能登大雅之堂。直到宋代以后白话市场才有所扩大,出现了像话本、杂剧、讲史等以白话为主的文学创作体裁。其次,体裁方面,在文学的发展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想当然的看法:诗文是雅的,小说戏曲是俗的。这种按照文体类型来划分雅俗的做法,是不科学的。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各种文体最初都来自民间,后来逐渐由俗转为雅,因此就认为一切雅皆起源于俗,而俗最终走向雅,这种思维方式颇直线化,因为雅俗之间相互对立、相互转化,而不是单向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文学发展的代表成就,如唐诗、宋词、元曲。我们承认每一种文体因为产生时间不同、所处时代不同、与民间关系不同等原因而程度不同地带有雅俗色彩。各种文体本身用雅俗评价,还是有所比照地用雅俗评价,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一个时期的雅文学发展到另一个时期可能成为俗文学,而一个时期的俗文学发展到另一个时期可能成为雅文学。鲁迅认为:“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小器与大度之类。没有别人,即无以显出这一面之优,所谓‘相反而实相成’者,就是这。”(注:鲁迅:《论俗人应避雅人》,见《鲁迅全集》,第6卷,2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所以我们很难断然决定某些文体就是俗文学,某些文体就是雅文学,都只是相对而言。因此评判不同文体时,要强调雅俗的对立和转化、雅俗的辩证统一。应该用全面的观点去评判一种文体内部的变化,尤其对小说这种文体的雅俗变化。再次,表现手法方面,古代文学中雅俗的作者和读者不同决定了雅文学表现手法相对含蓄,俗文学表现手法相对直白。
古代文学的雅俗之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含义、价值体系、审美观念和审美追求,但是如何区分文学的雅俗则是一个难题。雅俗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这决定了文学艺术创新的道路,即要达到审美的理想境界,就要做到雅俗融合。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认为:“斯斟酌乎文质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雅、俗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提供了多义的可能。因此真正伟大的作品,应该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穿透力,超越一般意义上的雅俗界定,如此才能成为经典。
二、现代小说的严肃消遣之别
吴秀亮借鉴了余英时的关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观点,提出:“‘五四’雅俗小说事实上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小说发展中并行不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注:吴秀亮:《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新论》,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诚然,现代小说中存在雅俗之分。对于雅文学和俗文学,李复威认为:“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上看,雅文学是作家的文学,俗文学是读者的文学。作家文学意味着以作家为本位,读者文学则是以读者为本位。从某种意义上说,雅文学需要读者适应作家……俗文学则需要作家去适应读者。”(注:李复威:《雅与俗:从疏离走向合流——论90年代我国文学演进的新走向》,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钱振纲认为:“严肃小说与消遣小说是从创作态度或者作者与读者关系的角度对小说进行的分类。严肃小说的本质特征是以作者为本位,其创作是为表达作者的审美意识;消遣小说的本质特征以读者为本位,其创作是为了迎合读者茶余饭后消遣的审美需要。”(注:钱振纲:《清末民国小说史论》,7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从李复威对雅俗文学以及钱振纲对严肃、消遣小说的分析看,雅文学和严肃小说是对应的,俗文学与消遣小说是对应的,可见雅俗文学之间的关系与严肃消遣小说之间的关系也应是对应的,因此我们在探究现代小说雅俗之分时用严肃消遣之别取而代之。
钱振纲从不同角度对“严肃小说”和“消遣小说”进行区分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把二者作为两个相对的概念则有些不合适,“严肃”和“消遣”这两个概念外延虽然相对,但内涵却不相对,严肃小说是从作者的角度强调,而消遣小说则从读者的角度强调。范伯群说:“新文学界的很多作家的确是很严肃地对待人生的,他们企望发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启蒙文学的作用。但是‘严肃’不是新文学界的统一的标志;另外,说他们是从事严肃文学的,那么相对而言,通俗文学似乎就是不严肃的文学,甚至有‘玩世文学’之嫌。”(注:范伯群:《俗文学的内涵及雅俗文学之分界》,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这种观点也同样有一定道理,这说明用“严肃”一词修饰“小说”是缺少科学性的,但鉴于目前找不到合适的词语与“消遣”相对应,而严肃小说还是能够涵盖清末民初的政治或启蒙小说和五四新文学小说的,况且朱自清认为:“严肃这个观念在我们现代文学开始发展时是认为很重要的。当时与新文学的创造方面对抗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小说。他们的态度,不论对文学、对人生,都是消遣的。新文学是严肃的。这严肃与消遣的对立中开始了新文学运动,尤其是新文学的创作方面。”(注:朱自清:《文学的严肃性》,见《朱自清全集》,第4卷,47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可见朱自清认为新文学是严肃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消遣的,而且也把严肃和消遣作为相对的概念提了出来。综上所述,姑且用之。
汤哲声说:“要规定20世纪中国雅俗文学的划分标准,首先应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有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性。这一特性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学是在传统文化之中自我运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则是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冲突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刻的文化内涵就是用西方的文化观重新审视和评估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提倡就是要用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取代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在这样的文化观念中产生的中国新文学也就是用西方的文化观念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注:汤哲声:《20世纪中国文学的雅俗之辨与雅俗合流》,载《学术月刊》,2006(3)。)这意味着不能用评价中国古代文学的雅俗标准评价新文学。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雅文学、俗文学的分野相对清晰,有各自的读者,很大程度上对抗性不是很明显。但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到来、现代知识分子的崛起,古代文学的雅俗格局被打破了,比如“现代白话诗歌合法性的确立,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语言雅俗格局最终崩溃的标志性事件”(注:邓伟:《分裂与建构: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新变研究(1898—1917)》,3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同时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和文学,对清末民初的消遣小说进行排挤和批判,从而形成现代小说的雅俗之分,并且建立起了不同于古代文学雅俗分野的结构,即新文学和现代消遣小说的分野。
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诗歌、散文一直是文学的主流和正宗,而小说则是“小道”。庄子最早使用“小说”这一概念。《庄子·外物》中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其大意是:把浅薄的话修饰得很动听,目的是求取功名,这与智慧通达离得太远了。此处的“小说”就是小道。“小说”这一概念从此就流传开来。班固对“小说”定义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注:《汉书·艺文志》,见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201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可见小说指的是民间或私下流传的一些杂事、琐语等。而到唐传奇时,就拥有了和现在小说相当的独立叙事文体。尽管宋元话本及颇有特色的叙述形式章回体的出现使中国古代小说到达了一个高峰,但甚至到明清,小说仍旧是小道,地位并没有上升。因此“有一个观念,从纪元前后起一直到十九世纪,差不多二千年来不曾改变的是:小说者,乃是对于正经的大著作而称,是不正经的浅陋的通俗的读物”(注:浦江清:《说小说》,载《当代评论》,1944(89)。)。从小说的产生及定义看,小说就是“小道”,“小道”的含义一方面表达了小说低下的地位,另一方面含有消遣之意。可见消遣是中国小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人们认为消遣娱乐只是生命的附属品,既不能使生命奋发图强,又不是生命意义存在的必需品,充其量是人们多余精力的占用和花费,所以在几千年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小说一直不能登大雅之堂。中国古代文学的核心潮流依次表现为先秦散文、汉赋、魏晋小品、唐诗、宋词、元代散曲、明清小说,始终居于文坛核心的是诗歌、散文。在古代的特定历史时期,相对而言,小说整体处于“小道”地位,曾很长时间不被重视,例如清王朝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间断地禁毁小说,并认为:“邪说传奇,为风俗害,自应严行禁止……以端士习而正民心。”(注:叶易:《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16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鲁迅对此曾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注:鲁迅:《〈草鞋脚〉小引》,见《鲁迅全集》,第6卷,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并且认为“中国之小说”也是“自来无史”(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见《鲁迅全集》,第9卷,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的。有的学者认为:“‘小说’作为补充正史的一种独立文体,创制已久,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并不是文学意义的小说,它们只是文学意义的小说的胚胎形态,它们是属于子部或史部的一类文体。自唐代起,它的一支变异为传奇小说,揭开了作为文学的小说历史的第一页。”(注: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这一观点说明直到唐代才出现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可见中国小说出现时间较晚,因而相比诗歌散文地位要轻得多。但是唐以后到明清时期,小说的辉煌业绩令人不能再忽视小说的存在。
中国小说产生发展的大致轮廓为:先秦时期,小说尚处于混沌草创时期,结集成书并留存至今的只有《山海经》、《穆天子传》两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怪小说《搜神记》以及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成熟阶段,鲁迅曾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事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见《鲁迅全集》,第9卷,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宋代话本运用当时生动活泼的口语,叙事状物,与较为简古和时有骈偶句的唐传奇相比,无疑开创了中国文学语言的一个新局面。宋代话本发展到元代时已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一是开创古代白话小说之一体;二是由短篇到长制,开创了小说创作的新局面。明代小说继承宋元话本传统,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逐渐推向顶峰,代表作品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封神榜》、《金瓶梅》等。清代则出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最高峰《红楼梦》及数千年文言小说的精华《聊斋志异》。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相对于诗文的雅及核心位置,小说只能占据俗及“小道”位置,但小说界革命后,小说则蔚为大观,陈伯海说“雅文学由强大渐趋萎缩,俗文学由幼嫩走向茁壮,双方的优势各自在转化”(注: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9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以上是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发展的概况。其实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发展过程的初期存在两个大系统:从唐传奇到明“剪灯二种”,再到清《聊斋志异》,基本上只有列传体一种体制;而宋元以来,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中国白话小说基本上也只有说书体一种体制。众所周知,列传体来源于史传,而说书体来源于说话。因此它们分别构成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所赖以产生的直接源头。袁进认为中国小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士大夫创作的文言小说,一部分是先由说书艺人创作,后来由下层文人和少数士大夫加入创作的白话章回小说。”(注: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可见中国古代小说内部也有雅俗的区分,因此有学者把中国古代小说分为雅俗两个部分。认为雅的部分就是士大夫文人用文言写成的,比如《世说新语》、《搜神记》等。这部分小说最早起源于记载琐语、异闻和杂事的小说,这部分小说在宋人欧阳修写《新唐书艺文志》对小说这一概念进行清理时,被归入了子部小说类。认为俗的部分就是指宋话本及以后的很多白话小说。比如《京本通俗小说》中的短篇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其实这些白话小说都是从宋代话本演化而来。认为宋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为了满足城市市民的文化和消遣娱乐需要,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说话”的技艺,说书的艺人把许多社会事实和历史上的趣闻编成故事说给人们听,这些故事就成为所说的话本,即白话小说。这些古代小说中被称为俗的部分主要写言情、传奇、公案等内容的故事。(注:参见宋生贵:《“通俗文学”:概念界说的不确定与判断取向的游移》,载《徐州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1)。)由此看来,文言小说是“雅”,白话小说是“俗”。这是由文体、语言形式决定的雅俗。
然而从审美角度看,白话小说未必俗,文言小说未必雅,雅俗只是相对而言。随着时代发展,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学习,比如《三国志通俗演义》运用《三国志》等史料,语言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因此既不能单纯从语言方面判定雅俗,也不能因为语言载体不同便把小说划在雅俗不同的范围内,比如《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但又不能说它是纯雅小说,又如《红楼梦》广采博收,兼纳并蓄,熔诗、词、赋、曲、铭等各种文体于一炉,集文言白话成就之大成,又运用以北方口语为基础而又高度加工提炼的文学语言。如果单纯按照文言与白话标准判定其雅与俗,则非常困难。阿诺德·豪泽尔说:“精英艺术、民间艺术和通俗艺术的概念都是理想化的概念,其实它们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出现的。艺术史上出现的艺术样式几乎都是混杂形式。”(注:[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207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所以古代小说初期根据语言判断雅俗的标准不是全面的,只是相对而言。根据语言判断雅俗的标准即使在小说界革命后也值得商榷,例如《新中国未来记》是白话却不俗,《玉梨魂》是文言却不雅。袁进认为:“文言小说的‘俗话’和白话小说的‘浅近文言化’,实际上通过小说这一文体作为媒介,使书面语中文言白话的对立趋于合流,终于在现代白话的基础上融合文言及外来语词语法,形成新的‘现代汉语’。”(注: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10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可见,把语言的文言或白话作为判断小说雅俗的唯一标准很难成立,小说的雅与俗只有在彼此对峙中才成立。
陈平原认为:“小说雅俗之分,只是一种假定性理论。我们可以用一系列二元对立来初步描述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如先锋性/大众化、独特性/程式化、探索性/娱乐化、精神性/商品化等,可很难再做进一步详细的辨析。”(注: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10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同时他还说:“而在中国古代,小说处在整个文学结构的边缘,‘雅’、‘俗’的分化并未真正形成。只是在梁启超等新小说家把小说提高到‘文学之最上乘’之后,雅、俗小说的对立才构成一对真正的‘矛盾’。清末民初是这一‘矛盾’的酝酿形成阶段,不管是严肃小说还是通俗小说,都不具备典型特征,而只是初具规模的雏形。”(注: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9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陈平原的观点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小说的雅俗之分只是一种假定性理论,小说的雅俗对立在清末民初只是处于酝酿阶段,不具备典型性。这意味着小说雅俗的转换品即真正意义上的严肃小说与消遣小说并未形成,相应的对峙也并未形成。相对于诗文,中国小说在新小说产生以前是整齐划一的,集体处于“小道”地位,没有小说功用方面的分歧,都是以消遣娱乐为主要特征。正因为如此,清末民初之前,中国小说不可能有严肃和消遣之区分,只有到了清末民初,新小说产生之后才可能在小说文体内形成对比,从而产生雅俗的转换品严肃与消遣。但是清末民初的严肃小说在形式上采用章回体等传统小说形式,目的是尽量满足市民大众的阅读需求,这与小说内容上的雅化存在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决定了这一时期的严肃小说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严肃小说,也就更无法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严肃小说。清末民初的严肃小说尚且如此,消遣小说当然更无法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消遣小说,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严肃与消遣之对峙无法成立。
小说界革命的结果是把小说称为文学之最上乘,誉为文圣之作,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第一次把小说从“稗官野史”提升到为改良社会服务的地位,传统的小说观念就此被打破,所谓“佐经书史传之穷”,“寓劝善惩恶之旨”等陈规滥矩的限制被抛弃。虽然小说创作仍继承了古代小说的诸多艺术形式,但是小说地位的提高和小说观念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小说创作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政治小说的产生,使雅俗判断的标准由形式变为小说主题是否严肃,能否启发民智,是否具有启蒙性。对此,王富仁提出了支持性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区别在于文学意蕴的高低优劣,而不在于它是否易懂易读。为什么赵树理的小说不是俗文学而是雅文学?因为他的作品的意蕴能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价值系统当中获得社会意义的说明。为什么大多数鸳鸯蝴蝶派小说和黑幕小说不是雅文学?因为它们在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学说中找不到对于它们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崇高意义的说明,这些作者也大都不以美学的和社会意义的追求为自己的创作目的。他们的创作以单纯迎合读者阅读趣味(不等同于我们所说的美学趣味)为目的而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注: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2)。)陈平原认为:“着意启蒙的文学不可能是真正的通俗文学”(注: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10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这个观点也印证了小说雅俗的判断标准主要在于主题的内蕴。梁启超等人的政治小说(启蒙小说)的出现,标志着小说被作为社会革命的工具。
从雅俗的角度看,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在提高小说地位的同时也取消了小说的消遣娱乐功能,把载道的功能转移到小说身上,小说因为载道启蒙而获得了雅文学的地位,因此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是对一种传统文学雅俗观的革命。有不少的政治家、文学家都希望通过小说的宣传和启发作用来达到既定的政治目标,从此小说不再作为单纯的娱乐对象,而是被赋予严肃性。小说界革命后,小说创作有一定政治目的,形式上对古代小说也有一定程度的疏离,注重加强作者主观意识的叙述方法的表达,这无疑突出了小说创作的严肃性。辛亥革命失败后,由于各种政治原因,特别是因城市繁荣和商品化市场形成,强调小说的消遣娱乐功能,最终引发消遣小说的兴起。严肃小说和消遣小说历时性存在于清末民初,但内容方面的差异和对立显而易见。综上所述,小说界革命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近现代小说雅俗之间的对立,即严肃和消遣的对立。但现代小说严肃消遣之真正意义上的对峙,则出现在“五四”以后,即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消遣小说的对峙。
陈蝶衣认为:“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本来只有一种,自古至今,一脉相传,不曾有过分歧。可是自从‘五四’时代胡适之先生提倡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文学遂有了新和旧的分别,新文学继承西洋各派的文艺思潮,旧文学则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虽然新文学家也尽有许多在研究旧文学,填写旧诗词,旧文学家也有许多转变成新文学家,但新旧双方壁垒的森严,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注: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载《万象》,1942(4)。)可见在五四时代中国文学开始有了明确的新旧之分。这样一来新旧文学在文学内部就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对峙。这种对峙主要体现于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消遣小说之间的对立。赵孝萱认为:“不应将‘新文学’与‘鸳派’以雅俗立场对立相称,因为它们的区别不在‘雅’‘俗’,也不在思想或是启蒙意义的高低,而只在语言形式与叙述情调的选择上。”(注: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22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这种观点确有些偏颇。因为五四文学革命后,白话作为国语被确定下来,新文学和现代消遣小说都用白话进行创作,白话不再是区分雅与俗的标准之一,而内容和创作形式的不同尤其是思想意蕴的不同成为区分它们的标准。新文学重视启蒙和反封建,重视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教育作用,同时受西方文学影响,运用了现代艺术手法;现代消遣小说虽然包含对现实的认识和思考,形式上也有所改进,但注重的仍然是消遣和娱乐,继承的依然是传统艺术手法。此外,五四时期新文学对现代消遣小说的严厉批评加深了它们之间的分歧。新文学和现代消遣小说在五四时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对峙。随着文学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仅仅对立,而是既对立又互补,并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转化,即新文学的俗化,如赵树理的小说,以及现代消遣小说的雅化,如张恨水的小说,甚至还诞生了超越雅俗的小说。这恰好与雅俗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相应合。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现代消遣小说在新文学精神的影响下发生了诸多变化,而且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但就“五四”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这个时段而言,新文学与现代消遣小说一直处于对峙状态,正是这种对峙成为中国小说发展的重要动力。(注:参见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10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他在《雅俗对峙》一文中写道:“我们更倾向于将通俗小说的崛起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将雅俗对峙作为促使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