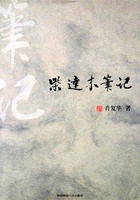
因为沙漠
一晃离开家已十几年了,久别重逢的家人都来接我,我和他们一一握手拥抱,但当我把手伸向他时,那灯熄了。
今年(2004年)春节,我在北京他在敦煌时还在电话里相互问候:我想你!我也想你呀!说完这句话,一切都在不言中了。春节一过,我再给他打电话,他却永不能再接听了,而是他的一个朋友在他家中接的。我还没问清情况,他便失声痛哭了起来,电话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呼喊:“继成啊继成,肖老师看你来了,看你来了……”

图为将生命留在青海油田的徐继成
放下电话,我用颤抖的手打开了他留给我的那本书——《洪荒岁月的风》,仿佛一下就握住了他的手。那洪荒的风又把我带回到了柴达木的岁月……
1985年,满二十岁的他大学毕业,完全可以留在大城市工作,但他却回来了,回到了一个生他养他、名叫“冷湖”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写下人生的第一首诗:
昨天,因为沙漠我离开沙漠
今天,因为沙漠我回到沙漠
不是走投无路
昨天我正年少
已不再年少的他,一回来便高扬起他们这一代自我生存柴达木的价值大旗,在《血脉相连》一文中,他如此地呼喊道:“我们来啦!我们来啦!面对被旷古之风蛮荒已久的土地,我们忘情地、玩命地呼唤着:我们来啦!我们来啦!”
他开始面对他的父辈发问:“你们这一代在柴达木奋斗了三十年,只落个创业者的虚名,你们不感到遗憾吗?”
父亲答非所问:“你们不能因为是钻井工人的儿子而感到遗憾啊!”
这个柴达木第一代钻井工人儿子的发问其实是在叩问自己日臻成熟的心。在高寒缺氧不见一根草的戈壁大漠打了一辈子井的父亲,老了,倒在了病床上,青春、血汗甚至生命的付出,究竟为了什么?用“无私奉献”的口号来诠释,实在显得过于苍白无力。呐喊着“我们来啦”的徐继成这一代开始了“手足无措的徘徊、彷徨、惆怅地苦苦求索。”苦苦的求索,使他坚定地走上了文学苦旅之路。
当时,我正在报社当编辑,柴达木石油文学尚在荒芜期,好稿子不多,若有也如戈壁的雨,落地就干涸了。然而他的一篇《厨房的哲学》却让人眼前一亮,他这样写漏勺:“漏勺,就像撒网捞鱼一样,我从来就剩下对主人有用的东西。”
对于用“漏勺”过滤生活的人,我倒真想见见。一见面,第一印象是他的岁数比他户口本上的大了不少。黧黑的脸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像是笼罩着大戈壁风沙的沧桑。两杯酒下肚,刚刚握手时“嘿嘿”一笑的孩子状便荡然无存了。谈起国事家事天下事,他都有他的见地。在柴达木长大的他,那“漏勺”般的思维方式超过了他二十岁出头的年龄。
果然,谈及文学,他又摆出一副纵论东西南北的派头,绕了一圈儿绕到了我的头上,他说:“我可不是拍马屁,因为你和我们一起吃苦,因为你和我们一起玩命写,在戈壁大漠中写下的字字句句在我们心里都是金沙,因为咱们是在给无历史的瀚海写下历史。”
我说:“你喝多了,话多了。”
他又“嘿嘿”憨然一笑:“见了你高兴,其实平时我没那么多话。”
是,平时他话是少。圈里人开个会,外边来作家开个会,他总是扶着眼镜静听,从不发言。可我知道他心里有数,作品是最好的发言。这几年,他的小说、散文如他醉后的酒话“突突”地往外冒,连得几个大奖,还加入了省、部作家协会。可我还是不断刺激他:“想当作家,你得伸拳头,拿大作品。”
他又是“嘿嘿”憨然一笑:“作家,与我早了点。我只是用心尽力去写。”这或许是柴达木作者自我封闭的一大弱点,但细想,这何尝又不是一个大优点呢?眼下的文学,有的人敲开门后就把敲门砖换成抹桌布,用过就扔了;有的人举着旗子招摇过市一阵子,那旗子就当成遮丑的屁股帘子了;有的人干脆把美好的文字复印为铜臭熏天的擦屁股纸了。守住一方净土,难能可贵。更何况他正经的职业是财会,并且大小也是个科长呢。
1995年,我正在编一本书,约他写他熟悉的柴达木的献身者。不几日,他便送来《平平淡淡才是真》、《深深缘》、《西去路上的祭坛》等,他写了他父亲那一代几位先行者,他这样写道:
父亲的战友们开始死了,他们都是三十岁以前进入柴达木的,经历三十多年风风雨雨,创建了一个油田,养育了一代人,现在开始死了。每每噩耗传来,父亲总会用严肃而缓慢的口气对我说:“事情从你们头上开过了。”我知道父亲指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果然就这样开始。或许,这“事情”验证了他写的话:“其实我也后怕,三十岁以后的日子不好过。
编完了那本书,我就调回了北京。不久,传来他撰写的电视片获西北五省奖,我心里很为他高兴。后来,朋友来电话说他又升了,升副处长了。当时我真是担心大于喜悦,他在一篇文中这样写道:“苦心经营当科长的当不上,不想当科长的却让他当,不颠倒多好。”为文者不是不能当官,而我却格外看重为文者当官后别人对他的称呼,如整天“处长,处头”的在众人口里捧着,他本色就没了,迟早“晕车”。

图为作者与徐继成的家人:其子徐海文(右二)、其妻李秀君(左一)、其姐徐继萍、其友刘冬海在一起。
还好,电话里的朋友依然在叫着他的外号“大头”,那一口一个“大头”,叫得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我知道,他在为官与为文的夹缝中艰难挣扎,但他的骨子里钟爱的依旧是文学,要知道,在这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油田,是不生产作家的。要想当一个真正的作家,是要坚忍住煎熬的,直到耗尽最后一滴血。这与我们,是悲哀的;而与他,那是骨子里无法更改的忠诚与追求。朋友告诉我,那天上午为大头送行,是他看到的追悼会来的人最多的,由此可见他的人品和文品。我默默点头为继成欣慰。当我见到他妻子和儿子徐文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不知我能为这娘俩做些什么。我的嗓子彻底失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心中默默地念诵着他二十岁那年写的诗句,当又一个二十年过去时,这诗竟成了他的墓志铭:
昨天,因为沙漠我离开沙漠
今天,因为沙漠我回到沙漠
这真是好诗!汽车驶出很远,我回过头去,向他挥着手!
因为沙漠,他埋在了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