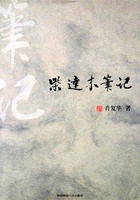
远飞的大雁
在敦煌,有一个叫盐池淀的地方,现在人称“大雁坞”,那里是敦煌海拔最低的地方,有一望不到边的大池塘,养有成百上千只大雁。我这只“远飞的大雁”,只看过天空上的大雁,只看过电影、电视、照片、图画上的大雁,只听别人唱过、自己也唱过的大雁,但能如此零距离的和成群结队的大雁在一起,与我生平尚属首次。
好友段绪勇就像看见了我的心一样对我说:“怎么样,你一到敦煌,我就告诉你,我一定带你到一个你去了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大雁不是候鸟了,它们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安家落户了的大雁,让我浮想联翩……
小时候最爱唱的一支歌是:我们是一群高飞的大雁,把“人”字写在祖国蔚蓝的天空上……那时,儿时的梦想天真烂漫在遥不可及的天上。
“文革”时,有一支歌我最爱唱: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来,捎个信儿到北京呀,翻身农奴想念恩人毛主席……那时,唱起这支歌,没有不热血燃烧、热泪盈眶的,尤其是在外地时;尤其是受压孤独无助时;尤其是十七岁的我们离开北京自愿来到柴达木一个寂寞的野外队时。唱起这只歌,就以为恩人毛主席一定能听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光芒四射的神圣一定会笼罩我们,使我们更加坚定“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
飞天般的大雁能“鸿雁传书”,也能“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更能“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因此,大雁是飞翔的信使,寄托着我们悠悠的情怀、绵绵的思念;大雁是精神的天使,放飞信天游笑迎仙客来。可以说,世上没有哪一种鸟能与人类在精神境界上的交流如此深层次的默契。天地人合一,感应着一个偌大的磁场,灵感由此生发:当大雁“人”字形列阵以每小时八九十公里的速度穿云破雾展翅高飞时,人们只能仰慕而叹,欲与天公试比高,然不能飞矣;当大雁从容栖落在河畔溪间池塘,高功不居闹市不染野花不采,掬一池碧绿抖落一身疲惫洗净一路尘埃,平凡与家鸭鹅共嬉戏;人禁不得不自悟,居功自傲怀才不遇追名逐利,上不得蓝天下不见碧水,捧一把烦恼堵死针眼大的心胸,自找一双迷障遮住黑色的眼睛,唯不见大雁顽强的毅力、团队的精神、平和的心态、冬去春来的自然规律。

盐池淀,敦煌海拔最低的地方,现在人称“大雁坞”。图为作者(右二)与武金弟(左二)等友人扬起手臂似大雁飞翔
与我们同车而来的消防保卫处处长武金弟一家三代都来了,见到那一人多高的团团红柳,他都要抱着他那才一岁多的小孙子武可照相。他捧起一把红柳叶对我说:“你仔细看,这叶子是针状,毛细管很细,便于吸收水分。这叶面是白色的,反射强光。大沙暴袭来时,它针叶张开,沙暴擦肩而过,红柳丝毫无损。酷日暴晒,它与大漠相融同造反射共抗烈日。不管环境多么险恶,生命自有生存的绝招。”他指着一群大雁说:“你看这大雁,是有灵性的。不管飞得多高多远,它认家恋家,就像你们北京学生,四十年不是还要回到戈壁大漠寻根访故吗……”我知道,武金弟已是四代同堂于戈壁大漠了,他与柴达木风云际会三十多载了,已是很西部的柴达木人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认家恋家、燕雀衔泥般一点一点建设着自己美好家园的大雁。

图为作者与段绪勇在去汉长城的路上
告别大雁,我们继续西行。一望无垠的大漠,浑黄中跳跃着血色花红的红柳,像是一座座烽火台点燃着生命的信息。人迹罕见了,汽车也走不动了,但见远方风蚀残丘雅丹恍如海市蜃楼。段绪勇对我说:“我们走过去看看吧。”那不是自然的造化,而是生命千年不朽的象征!那是一座用生命的鲜血搅拌足下的黄土筑起的汉长城,魏武扬鞭千年而过,血肉长城依然接着地、连着天。“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当年汉将军李广屯垦戍边种杏栽柳,恐是“雁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吧,但将军“愿随孤月影,流照伏坡营”,朝日出阳关,挥师玉门外,血染疆场,脚踏匈奴,收复失地。雁南归时,将军留下回味无穷的李广杏,千年不倒的汉长城。我们像一群大雁,飞到汉长城的烽火台上,举一把红柳燃烧起血与火的信息,告诉远方的大雁,冲天而起划天而过的瞬间,只要珍惜,便会留下永恒。春天的浪漫已是回忆,夏日的喧嚣萦绕余音,秋之境落下回想飞向希望,飞吧,我们的大雁……

图为作者与妻子离开大雁坞,一路西行
一路,那静态的长城,那动感的大雁如天地合一的中国画悬挂在敦煌的天地间。再过大雁坞,“人”字雁阵高翔在天,那是天然的万里长城,只有仰望星空的人才能看到,才能欣赏,才能与雁同飞共舞进入寻常百姓家。此时,儿时的“雁歌”不会唱了,“文革”时的“雁歌”不愿唱了,那是因为我听见并听懂了大雁的歌唱。啊,我们的大雁啊,我该唱支什么歌给你听呢……